第五讲 希腊实在论哲学
柏拉图哲学
希腊的实在论哲学,也就是讲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他们的哲学可以说是达到了希腊哲学的顶峰。
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出身于雅典的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其家族中既有雅典民主制的政治家,也有雅典寡头政治的参与者。柏拉图既是苏格拉底的嫡传弟子,也是亚里士多德的授业老师,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师徒三人,通常被称为“希腊哲学三杰”,无可争议地代表着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
柏拉图与德谟克利特,两人分别代表了希腊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的最高成就(亚里士多德哲学则是对二者的总结),但是其历史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这确实是一件令人感叹的事情。
这种普遍性的“实体”被以往的思想家们命名为“数”、“逻各斯”或者“存在”,这种致力于寻找背后的实在者的形而上学传统构成了柏拉图理念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此外,柏拉图早年在投到苏格拉底门下之前,也曾拜过爱非斯学派的克拉底鲁为师,克拉底鲁关于“万物皆变,无物常驻”的思想对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造成了他对现象世界的轻视。当然,除了这些人以外,对柏拉图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寻找关于事物的一般定义、探讨事物“本身”的做法,成为柏拉图理念论的直接思想来源。
在柏拉图那里,事物“本身”或者一般定义就被叫作“理念”(idea或eidos)。
他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方面:第一,苏格拉底虽然致力于探讨事物“本身”,通过归纳推理来寻求事物的一般定义,但是他所探讨的美德、正义、善等事物都是主观精神世界的道德范畴,他并没有去探讨自然界和客观世界的事物“本身”;但是柏拉图却把这个“本身”由纯粹的主观精神世界的道德范畴推广到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每一种事物都有“本身”,都有作为其存在之根据的“理念”。
第二,苏格拉底虽然注重事物“本身”,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说这个“本身”是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它只能寓于具体事物之中,
但是柏拉图却把事物的“理念”与具体事物完全割裂开来,“理念”获得了客观独立性,成为一种客观概念或者客观精神,它不仅独立于具体事物而存在,而且构成了后者存在的根据,甚至在知识论上还与后者相互对立(真理与意见的对立)。理念独立于并且先于具体事物以及我们的头脑而存在,具体事物是对它的一种摹仿和分有,而我们头脑中的理念则是由灵魂带入到身体中来的。这样一种观点,通常就被称为客观唯心主义。但是由于唯心主义这个概念是近代的哲学概念,所以我们毋宁用形而上学实在论来指称柏拉图的理念论。
柏拉图的理念论把精神性的东西“理念”当作唯一真实的存在或实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他的哲学称为实在论哲学。
世界上首先有了万事万物的理念,然后才会有万事万物。
在任何具体事物被创造出来之前,它们作为观念或理念已经存在于上帝的心中了,万事万物无非是对上帝心中观念的一种现实化、分有和摹仿罢了。柏拉图所讲的客观理念,就是上帝头脑中的那些思想,只不过上帝本人却是缺席的。大家去掉上帝但是却保留他头脑中的观念,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了。
结果不能大于原因
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柏拉图虽然认为理念是存在,但是他并没有像巴门尼德那样把处在流变之中的感性事物当作非存在,而是认为它们处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在柏拉图那里,真正的非存在是指那些构成感性事物的质料因素——原始“物质”。很明显,被柏拉图当作非存在的原始“物质”,恰恰就是被他的哲学对手德谟克利特当作万物本原的“原子”。而且柏拉图也没有像巴门尼德那样在存在与非存在之间画下一条泾渭分明的质的分界线,而是通过一种量的层级逐渐实现从非存在到存在的过渡。在作为最低层的原始“物质”与作为最高层的“善”的理念之间,有着一个由感性事物和各种理念构成的实在性程度各不相同的量的层级。感性事物都是由原始“物质”(非存在)分有和摹仿各种理念(存在)而形成的,而所有的感性事物和理念又都以“善”的理念作为终极目的和根本动力。
在柏拉图这里,就已经把形式的东西同时也当作目的和动力了,从而把能动性从物质方面剥夺了(由此我们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与柏拉图相对立的德谟克利特为什么一定要强调原子是自动的)。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形式因、目的因、动力因三者统一起来,显然是受了柏拉图理念论的影响。
理念构成了感性事物的形式、目的和动力,但是理念本身却是多,它们构成了一个世界即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相对立。在理念世界中,也有等级之分,柏拉图将理念世界由低到高分为六个等级。最低一级是自然物的理念,如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的理念。
第二级是人造物的理念,比如桌子、椅子、床等的理念。第三级是数理理念,比如正方、长方这些数学理念。第四级是哲学范畴意义上的理念,如存在与非存在、静与动、一与多等。第五级是道德和审美的理念,像美、勇敢、正义、节制等理念。最高一级是“善”的理念,即善本身。这六个层级的理念,由低向高,下面的理念以上面的理念作为目的和动力,所有的理念又以“善”的理念作为终极目的和根本动力。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各种感性事物趋向于自己的理念,较低级的理念趋向于较高级的理念,所有的事物和理念都趋向于“善”的理念的井然有序的世界模型和本体论体系。
柏拉图的创世论与基督教创世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基督教的上帝是从虚无中创造世界的,而柏拉图的“善”或者德穆革却是将理念加到原本就具有的原始“物质”之上,使它获得形式而成为具体的感性事物。
与处于世界最顶端的“善”的理念所具有的实在性和能动性相比,处于世界最低层的原始“物质”是一种没有任何形式规定、缺乏任何实在性的非存在,它只有通过对各种理念的分有和摹仿才能获得形式,成为某种现实的感性事物。
理念提供形式(以及目的和动力),原始“物质”提供质料,二者相结合而构成形形色色的感觉事物。这个思想是在柏拉图理念论中首先表述出来的,后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总结为“四因说”理论。形式与质料的结合同时也代表着古希腊两种哲学潮流的合流,因为柏拉图所说的原始“物质”或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纯质料”,恰恰就是被希腊自然哲学当作万物本原的基本元素或物质微粒。
这种在逻辑上把形式看作先于质料和高于质料的观点,导致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主张思维先于存在、精神决定物质的唯心主义哲学。
柏拉图在本体论上将理念世界、感觉世界和原始物质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与此相应,在认识论上,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就被叫作真理,对于感觉世界的认识就被叫作意见;而对于原始物质,我们不可能有任何认识,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可被认识的形式,所以关于原始物质,我们只有无知。相对于无知而言,真理和意见都可以纳入知识的范围,但是二者的可靠性程度却大相径庭。真理是真知灼见,而意见却是靠不住的大众常识。
我们所熟悉的唯物主义在认识论上是主张反映论的。按照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我们的一切知识首先是从对具体事物的感性认识开始的,然后通过抽象思维的作用,从感觉、知觉、表象等感性认识上升到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形成普遍性的知识。但是柏拉图的看法却与此相反,正如他在本体论上认为理念是独立于和优先于感性事物而存在的一样,他在认识论上也认为,关于理念世界的知识完全不依赖对感性事物的认识;而且从逻辑上和时间上来说,我们是先有关于理念的知识,然后才有关于感性事物的知识。
这种关于理念的知识如果不是来自感性认识,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柏拉图的回答非常明确,它是与生俱来的,是灵魂从外面带入到我们身体中来的,感觉经验充其量只是刺激它重新呈现出来的触媒而已。这种观点在哲学史上通常被叫作先验论,即认为我们的真理性知识是先于经验而存在于我们思想之中的。柏拉图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先验论的开创者和重要代表,他的这种先验论也被叫作“回忆说”。
关于柏拉图的“回忆说”,有几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柏拉图虽然认为知识的来源是灵魂中固有的理念,而不是感觉经验,但是他并不否认感觉经验是刺激我们回忆起知识的触媒或机缘。
第二,柏拉图所说的那种灵魂所固有、后来被遗忘、再后来又被回忆起来的知识,并不是关于具体事物的知识,而是关于理念的知识。
第三,柏拉图认为回忆本身也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我们不断地从无知到有知,再到更高的知识,最终实现对“善”的理念的知识。在这个不断上升的过程中,灵魂表现出一种能动的作用,正是这种能动性,使得理念知识逐渐从潜在状态转变为现实状态。
这个“洞喻”所展现的整个认识过程是:首先是对假象的假象(木偶的影子,比喻对感性事物的摹仿,如艺术品等)的认识,其次是对假象(木偶,比喻作为理念之摹本的感性事物)的认识,再次是对实物(真实的人和物,比喻理念)的认识,最后则是对照耀实物的万物之源(太阳,比喻“善”的理念)的认识。而这种知识的上升过程,恰恰是通过灵魂的不断“回头”、不断反思才得以实现的。
与这个“洞喻”相呼应,柏拉图又提出了一个“线喻”,他用一条线段来说明知识的不同阶段。一条线从中间分为两段,左边一段叫“意见”,右边一段叫“真理”。“意见”对应的是感觉世界,“真理”对应的是理念世界。当然还有一段没有画出来,那就是对应于原始物质的“无知”,它根本就不属于知识的范围。“意见”这一段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段,一段叫作“想象”,另一段叫作“信念”;“真理”这一段也可以分成两段,一段叫作“理智”,另一段叫作“理性”。
“想象”的对象就是指感性事物的摹仿物,例如感性事物在阳光下或水中的影子,艺术作品对感性事物的临摹和表现等,柏拉图将其视为“摹本的摹本”。因为感性事物本身就是理念的摹本,而对感性事物的摹仿当然就是“摹本的摹本”了。正因为艺术品属于“摹本的摹本”,是最低级、离真理最远的知识,所以柏拉图特别轻视艺术。
“信念”的对象就是具体的感性事物,它们作为理念的摹本,在知识的可靠性上无法与真理相比,但是却比“想象”要可靠一些,而且它们也构成了刺激灵魂回忆起理念知识的触媒。上面这两类都属于“意见”,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感性认识。
第三类知识是“理智”,它的对象是理念,但却是一些较低层次的理念,如自然物的理念、人造物的理念、数理理念等。这些理念虽然是抽象的,但是仍然与形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还不能完全脱离形体。
最高的真理性知识是“理性”,它的对象是范畴,即纯粹的抽象概念。这些理念或概念已经完全脱离了有形的事物,纯粹就是在抽象思维中进行联系和转化,从一个理念推演出另一个理念,完全不需要任何感性事物的中介。而这种在抽象的理念或范畴之间进行纯粹的逻辑推演的理性知识,就被柏拉图叫作“辩证法”。
辩证法在柏拉图那里是以一种对立统一的形式展开的,柏拉图试图通过在对立概念之间寻求同一的方式,来超越以往的诡辩论。希腊诡辩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建立在相对主义基础之上的。诡辩论的特点就是片面地夸大事物的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个方面,比如克拉底鲁片面夸大连续性而否定间断性,芝诺则片面夸大间断性而否定连续性;而柏拉图的辩证法恰恰在于强调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它以一种全面的观点把诡辩论的两个片面真理都包含在内了。
理想国是柏拉图终生不渝地追求的政治理想,虽然没有实现,但是这种理论对于后世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斯巴达城邦作为楷模的,它实际上是斯巴达社会的等级制度与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相混杂的一个产物。
统治者的美德就是智慧,保卫者的美德就是勇敢,而劳动者的美德就是节制。如果这三个等级的人都各自遵循自身的美德原则,统治者勤于治理国家,保卫者勇于保护国家,劳动者则恪守节制的美德,服从第一、二等级的统治,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正义的国家,即“理想国”了。
除非哲学家变成我们国家中的国王,或者我们叫作国王或统治者的那些人能够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哲学,使得哲学和政治这两件事情能够结合起来,而把那些现在只搞政治而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人排斥出去,否则我们的国家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全人类也不会免于灾难。
在西方历史上,唯一把二者结合起来的人可能就是罗马帝国的皇帝马可·奥勒留。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公元2世纪下半叶当政的罗马皇帝尽管位极至尊,在哲学上却是一个极其悲观的斯多葛主义者;而且正是这位哲学家皇帝在政治上结束了安东尼王朝“五贤帝”时代的辉煌,开启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引擎。我们真不知道到底是政治扭曲了他的哲学,还是哲学戕害了他的政治?但是,至少这位历史上唯一的哲学家皇帝并没有给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提供强有力的正面证据,这一点却是确定无疑的。
亚里士多德哲学
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已经大体了解到古希腊实在论哲学的基本特点,那就是把抽象的理念当作真正实在的东西,而把感性事物当作一些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过眼烟云。理念与感性事物之间的这种对立又导致了认识论上的唯理论倾向,从而使逻辑思维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感觉经验的重要性,这就造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那种“眼见为虚,思想为实”的主导观点。
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发现了原子论与理念论之间的这种同构性,他在综合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更高水平的实在论哲学。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出生于色雷斯的一个城邦,17岁时就来到雅典,进入了柏拉图学园,在那里工作和学习了近20年。在此期间,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思想耳濡目染,了解至深,成为一个柏拉图主义者。
由于亚里士多德喜欢一边散步,一边对学生讲课,所以他的学派也被叫作“逍遥学派”。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实际上是一种弄巧成拙的学说,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我们本来是要研究那些实在的东西,即作为实体的个别事物,但是柏拉图却在个别事物之外又提出了一套理念世界,并且把它们当作具体事物的原因。
柏拉图主义具有显著的迷狂色彩,而亚里士多德主义更侧重于严谨的逻辑慎思,二者一个是神秘主义的,一个是理性主义的。
作为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中往往也会有一些前后相悖的矛盾之处,这是由于要把各种对立观点都融会于自身之中的妥协所致。妥协往往会导致矛盾,这种情况在西方哲学史上并不罕见。亚里士多德既然要把柏拉图和德谟克利特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包容在自身之内,他就难免会在一些地方表现出自相矛盾。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也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对古希腊的各种知识都进行了总结,在物理学(即广义的自然科学)、逻辑学、伦理学、文艺学、政治学等各方面都颇有建树,所以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古希腊学识的最高峰。
在当时的希腊,所有的知识都被纳入“哲学”之中,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严格地进行学科分类——亚里士多德本人把这部分内容称为“第一哲学”,即“关于存在本身的学说”。然而,这一部分如此重要的内容,既不能纳入物理学或逻辑学,也不能纳入伦理学或者其他任何学科之中,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们就把它们专门编了一卷,暂时放在《物理学》后面,取名为metaphysic,即“在物理学之后”。这个名称本来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是由于这部分内容被亚里士多德当作整个知识系统或广义哲学的基础,是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科学,所以“metaphysic”一词就具有了根本性和超验性的含义。后来,中国的学者在翻译这个概念时,取了《周易》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说法,把它译为“形而上学”,意指一种超经验的、高深莫测的根本之学。
最高的知识还要从技术上升到理论,从生产部门上升到理论部门,这种最普遍、最一般的理论知识才是最高的智慧。亚里士多德把它称为“第一哲学”(因为其他的知识也都被称为哲学),它的对象不是特殊的存在物,而是“存在本身”或者“作为存在的存在”。
第一哲学是研究存在本身的学问,而那些研究具体存在物的学问,如物理学等,就被叫作第二哲学。这种研究存在本身的第一哲学,后来被一位17世纪的经院哲学家郭克兰纽(R.Gocleneus)称为“本体论”(ontology)。这种探讨世界本体或实体的本体论,通常也被叫作“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可以把存在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偶然的属性,
第二类是必然的本质,即范畴,所谓“范畴”就是对各种事物进行高度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最基本的概念。亚里士多德把范畴分为十类,即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态、动作和遭受。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事物都必须具备这十类范畴,缺一不可,因此范畴是必然性的存在。
实体构成了其他范畴的基础和前提,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本身”或者“作为存在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哲学旨在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实体是什么?”,这是最基础性的问题;第二,“实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第三,“实体是如何生成的?”,这个问题说明了从实体的原因到实体的发展过程。这三个问题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实体哲学的基本内容,关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狭义的“实体学说”,关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导致了“四因说”,关于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潜能与现实”的理论。
无论是从逻辑定义上、认识上还是时间上,实体都是最初的东西;其他范畴都不能离开实体而独立存在,只有实体才是独立存在的。
实体,在最严格、最原始、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既不述说一个主体,也不依存于一个主体的东西。
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实体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它是“这一个”,即一个具体的和个别的事物;第二,实体不像属性,它没有与之相反的东西,例如与“大”相反的属性是“小”,与“好”相反的属性是“坏”,但是却没有一个与苏格拉底相反的东西;第三,实体没有程度上的差别,比如张三和李四作为个别的人都是实体,我们不能说张三比李四更是一个人;第四,实体是变中之不变,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无论是年轻还是年老,是满脸稚气还是满脸皱纹,他都是苏格拉底,他作为一个不变的实体承载着各种属性方面的变化。实体的这四个特点,更加鲜明地说明了实体是个别的事物,是与理念相对立的东西。
当亚里士多德用刚才那个定义来界定实体时,他所说的实体确实是指个别事物。但是他紧接着又强调,个别事物只是第一实体,除此之外还有第二实体,即种属概念。
亚里士多德承认,种属概念作为第二实体,不如第一实体那么实在,因为它只满足了上述定义的第二个条件(“不依存于一个主体”),而没有满足第一个条件(“不述说一个主体”)。
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种属概念具有独立实在性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这种独立实在性究竟只是一种逻辑上的独立实在性,还是一种现实中的独立实在性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它充其量只具有一种逻辑上的独立实在性。换句话说,所谓种属概念或者第二实体不过是一个只能在思维中存在的抽象概念而已。
他根据古往今来的各种观点,把实体的原因概括为四个方面的因素,即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由此形成了他的“四因说”理论。
当我们探寻一个实体或个别事物的原因时,我们会发现,这些原因无非可以归结为如下四个方面:首先,它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质料因);其次,它被规定成为什么样子(形式因);再次,是什么东西使它成为该事物(动力因);最后,为什么要造成它(目的因)。大家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实际上是对以往希腊哲学关于本原问题的各种答案的理论总结。
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造物上面,这四种原因是可以明显区分的,但是在自然物上面,这四种原因却可以被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料因,另一方面是形式因,而动力因和目的因都可以归于形式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任何具体事物都既有质料也有形式,缺一不可。但是,从整个世界的结构来看,质料与形式之间还呈现出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关系,即低一级事物构成了高一级事物的质料,高一级事物则构成了低一级事物的形式。
因此,一方面,每一个具体事物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另一方面,每一个高一级事物又是低一级事物的形式、动力和目的,而低一级事物则是高一级事物的质料。这样一来,整个世界就构成了一个从低到高、相对而言的质料与形式的动态系统和阶梯模式。在这个阶梯的最下端,是一个没有任何形式规定性的“纯质料”;在这个阶梯的最上端,是一个不再构成任何事物质料的“纯形式”。而在这两端之间,则存在着无数多的各个层次的实体或事物,它们每一个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体。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模型。
“纯质料”就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原子在构成具体事物之前缺乏任何形式规定性,因此它当然是一种“纯质料”或者柏拉图所说的原始物质了。而“纯形式”就是柏拉图的理念,它构成了原始物质或“纯质料”所趋向的目的和运动的动力。处于“纯质料”与“纯形式”这两端之间的整个实体世界(它们每一个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统一体),则是由柏拉图的理念加诸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或原始物质)之上而形成的各种感性事物。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过去的哲学家都未能真正地探讨这个问题。
与上述这些武断虚妄的观点不同,亚里士多德从有机论的角度说明了实体是如何生成的,创立了“潜能与现实”的学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实体的生成过程是一个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任何一个事物,在成为它自身之前,都处于一种潜能状态,只是一个潜在的东西。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潜能与现实并非两个漠不相关的东西,而是同一个事物的两种不同存在状态,因此它们是不可截然分开的。潜能与现实的关系,是和质料与形式的关系相对应的。任何事物的质料在没有获得一定的形式而成为该事物之前,都只是一种潜能。
这样一来,任何事物的产生就不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而是一个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
这种把事物的生灭变化理解为质料与形式、潜能与现实之间相互转化或聚散离合过程的观点,在希腊哲学中是非常流行的观点。不仅自然哲学家们是这样解释万物的形成过程的,而且连柏拉图的理念论也包含着同样的思想,即原始物质由于分有了理念而成为现实的感性事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作为潜能的东西已经内在地包含了现实所具有的一切因素,它与现实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它还没有实现为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观比两千年以后霍布斯、牛顿等人的运动观还要高明。后者仅仅是从力学或机械论意义上来理解运动的,即仅仅把运动理解为空间上的位移;而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运动则是指从潜能向现实的转化,这种理解既包含了机械论意义上的位移(因为位移同样也是一种从潜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同时也包含了有机论意义上的生长。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中明确地把运动形态分为六种,即产生与消灭(“本质上的变化”)、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性质上的变化”)、增加与减少(数量上的变化),以及位移(位置上的变化)。而所有这些运动形态,都可以理解为从潜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
亚里士多德的潜能与现实学说以一种辩证的和动态的观点说明了万物的生成过程,从而超越了柏拉图的静态分有说和原子论者的机械构造说。
按照这种有机论观点,万事万物的运动都是由于它们所趋向的那个目的推动的。虽然目的到最后才能实现,但是它却始终在事物的内部发挥着作用,驱策事物坚定不移地向着它前进。有机论认为,事物运动的动力来自内在的某种目的;机械论则认为,事物运动的动力来自外部的某种力量;有机论理解的运动是一种生长,而机械论理解的运动只是一种位移。就此而言,有机论的运动是内在的和主动的,机械论的运动是外在的和被动的。
当然,在亚里士多德的有机论中隐含着目的论的思想,它很容易导致有神论的结论(事实上,机械论同样也会导致有神论的结论,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有机论在解释运动时显然比机械论更加高明,它把动力归结为事物的内在目的,而不是外部推动;它把整个世界看作一个受内在目的驱策而不断生长的有机体,而不是一个受外部作用影响的机械物。当我们把世界看作一个按照某种既定目的而生长的有机体时,当然就很容易走向一种外在设计论,从而为神学提供一个根据。
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只是对进化结果的一种辩护,而不是对进化原因的一种说明。在科学无法提供终极性答案的地方,哲学和神学就会趁虚而入,建立起自己的解释理论。
后世的唯心主义会坚持和发扬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比质料更是实体的思想,以及形式构成了质料的目的和动力的思想;而后世的唯物主义则会坚持和发扬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实体比第二实体更加实在的思想。这种观点分歧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中就明显地表现出来,在近代西方的哲学家那里也不断地再现。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亚里士多德哲学看作像康德哲学一样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以前的水流都汇聚于它之中,以后的水流又都是从它里面流出去的。
![图片[1]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哲学】《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个人摘录(第五讲 希腊实在论哲学)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小竹の笔记本](https://img.smallbamboo.cn/i/2025/09/18/68cba8e7b2b8d.jpg)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662629/
说明:本文每一行均为部分摘录,阅读连贯性可能较差,个人存档用,推荐购买正版书籍阅读。
2. 论文总结类文章中涉及的图表、数据等素材,版权归原出版商及论文作者所有,仅为学术交流目的引用;若相关权利人认为存在侵权,请联系本网站删除,联系方式:i@smallbamboo.cn。
3. 违反上述声明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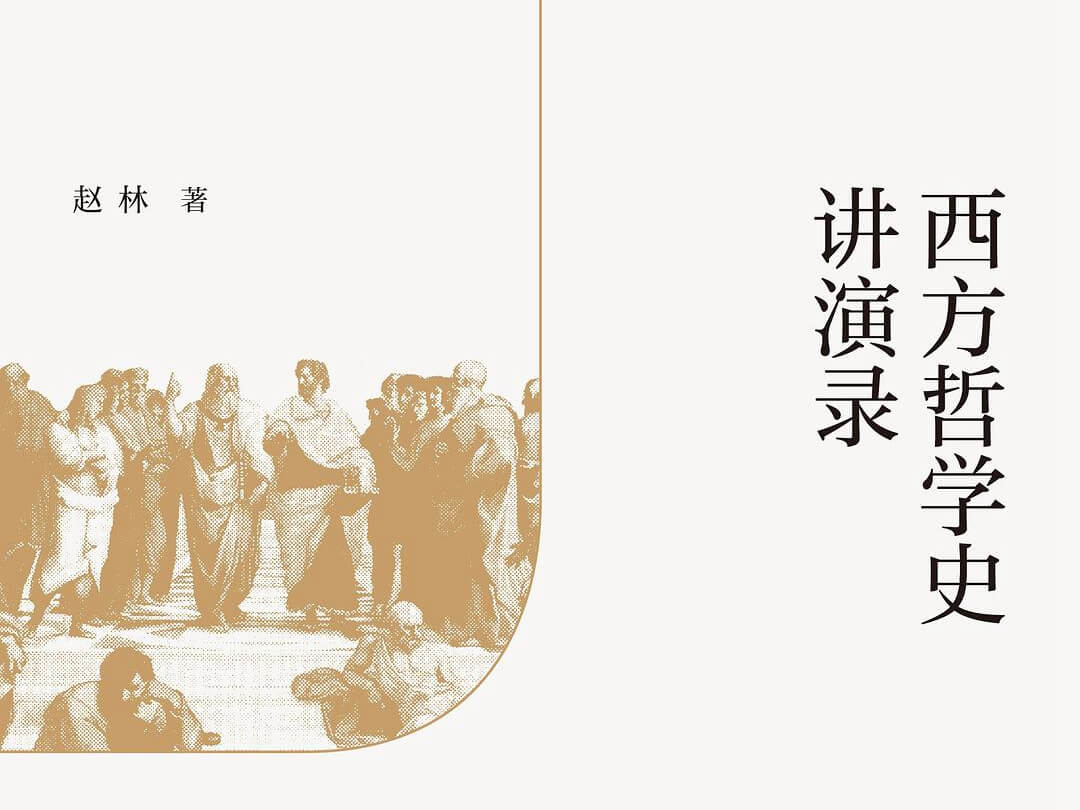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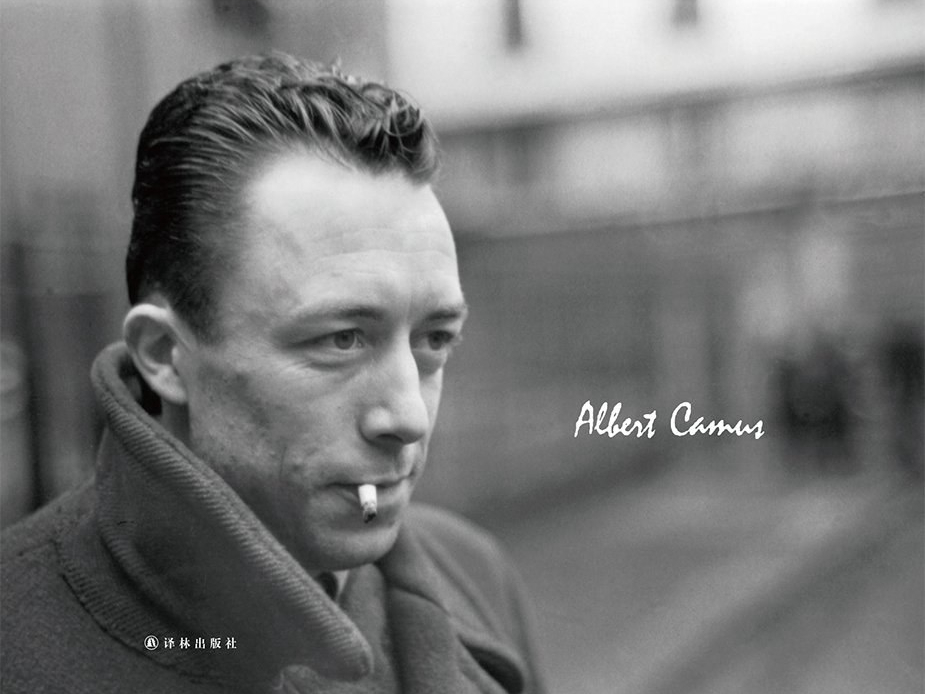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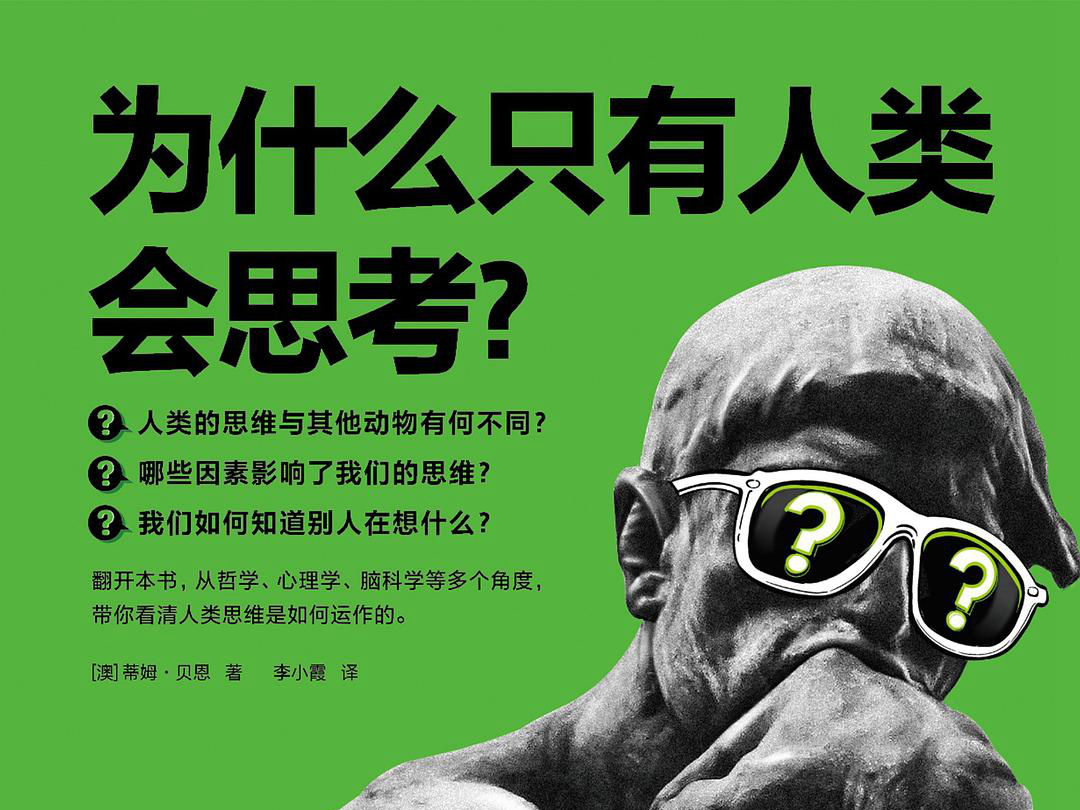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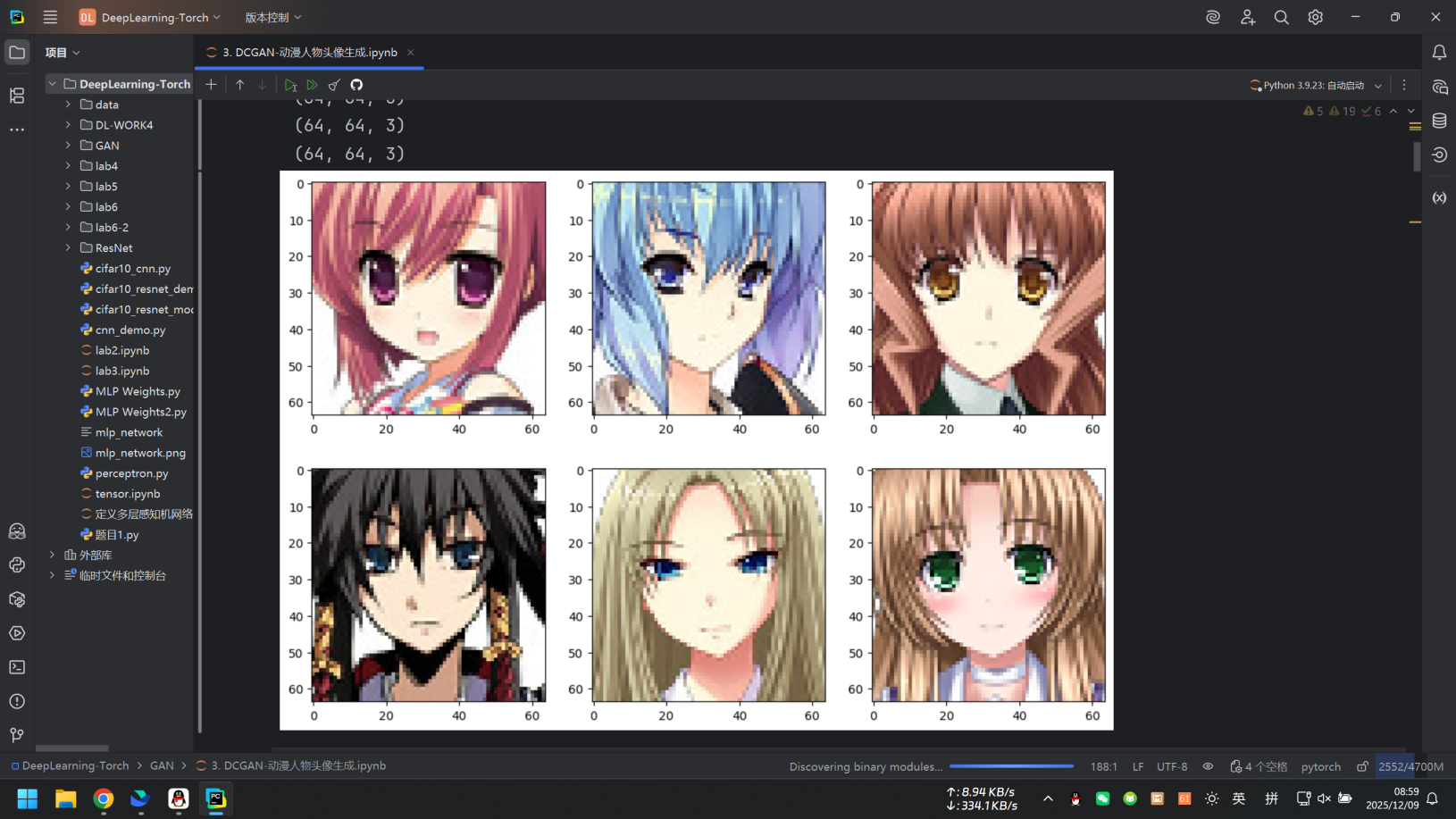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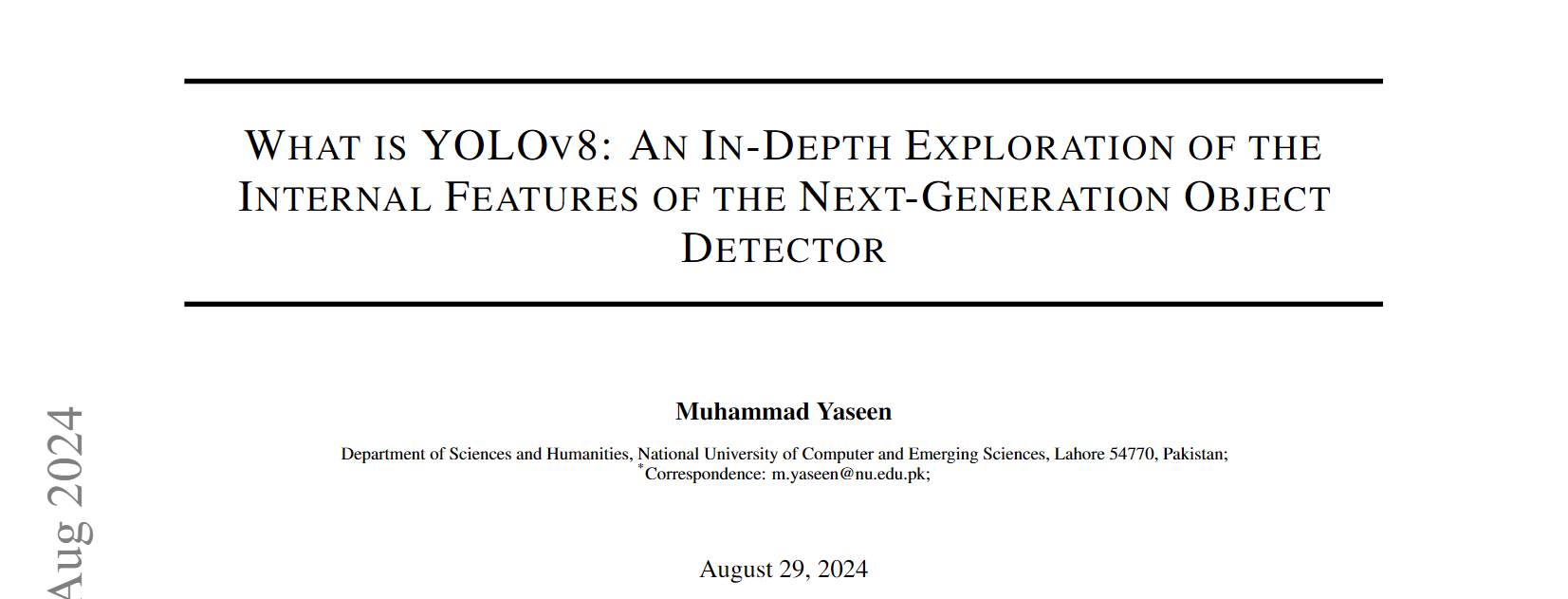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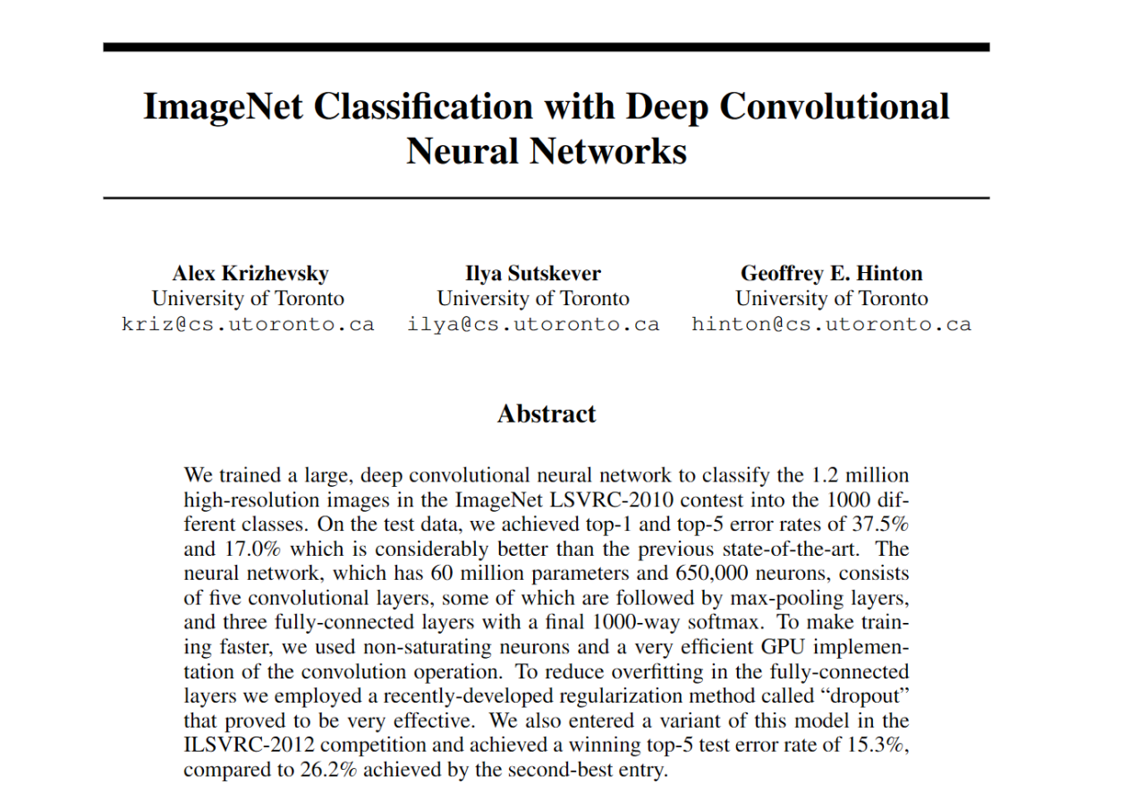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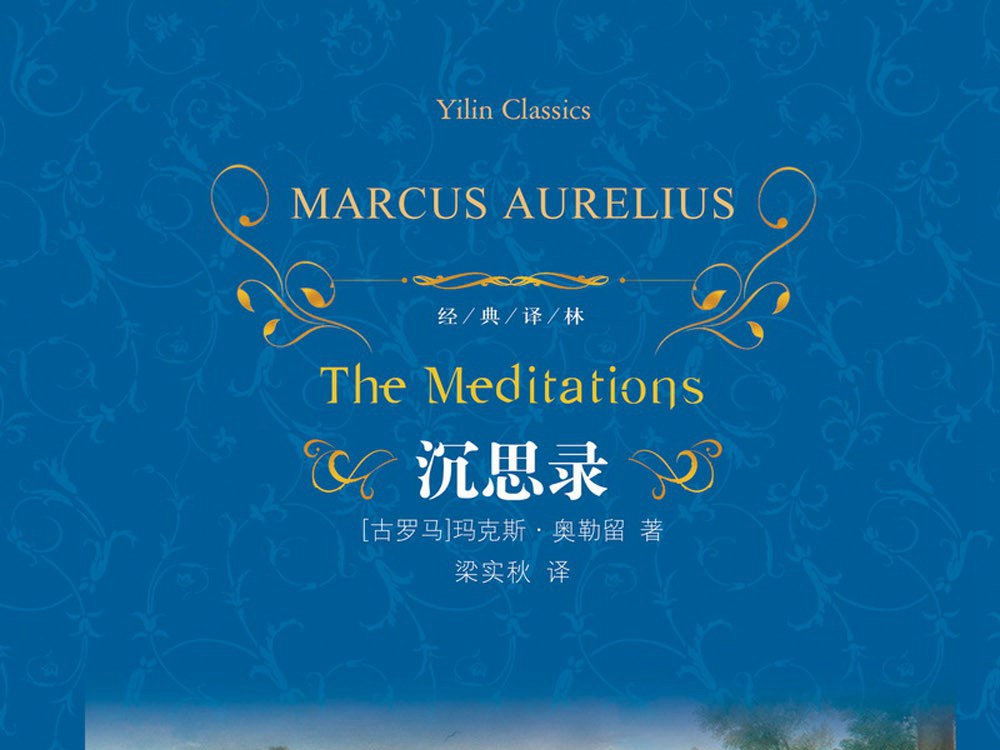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