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希腊哲学的衰颓
希腊化时代的三大学派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来说,希腊化时代以及罗马时期的哲学构成了古代希腊哲学与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之间的一个必要中介。因此,这一讲既可以叫作希腊哲学的衰颓,也可以看作基督教哲学的开端。
这里所说的东方文化,并不包括我们中国文化,基本上也不包括印度文化,而是指与希腊文化联系较多的巴比伦文化、波斯文化和埃及文化等。
人们不再关心世界的“本原”或“实体”,不再关心背后的东西,而是在东方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腐蚀下,越来越沉溺于现象世界的感性快乐。与这种社会风气相适应,希腊哲学也开始向着感觉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方向发展。哲学已经不再关心终极真理的问题,不再关心形而上学,而是蜕变为一种伦理学。
希腊化时代出现了三大哲学学派,它们分别是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
其中,伊壁鸠鲁主义与斯多葛主义后来甚至成为针锋相对的两种哲学或伦理学,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对立并不能消除它们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
它们共同思考的问题是:在这个不幸的世界里,人如何才能获得幸福?这样一种提问方式,恰恰是一种末世的提问方式,即一个文化时代发展到最后阶段的提问方式,它充满了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
伊壁鸠鲁(Epicurus)是希腊化早期的一位哲学家,他生活在公元前341—前270年之间。在介绍伊壁鸠鲁的思想时,我特别要强调一点,那就是我们应该把伊壁鸠鲁本人与后来的所谓“伊壁鸠鲁主义”区分开来。
其实,“伊壁鸠鲁主义”被等同于纵欲主义,这是一种以讹传讹的结果,对伊壁鸠鲁来说是不公正的。伊壁鸠鲁本人并不是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他绝不是一个纵欲主义者,相反,他倒是一个非常讲究理性,推崇节俭、朴素的生活态度的人,因此毋宁把他称为一个审慎的节欲主义者更为合适。
西塞罗是一位斯多葛主义者,他把“伊壁鸠鲁主义”与纵欲主义相提并论,败坏了伊壁鸠鲁的名声。
但是到了希腊化时代,伊壁鸠鲁却认为,哲学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寻找生活宁静之道”,说到底也就是追求幸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时代不同了,人们的提问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伊壁鸠鲁时代的哲学目的已经不在于求知,而在于帮助我们如何在一个纷扰不已的世界里摆脱痛苦,获得幸福。
哲学现在只是一种实践的智慧,即伦理学,除了如何获得幸福之外,它对什么都不再关心。
伊壁鸠鲁从一种消极意义上来理解幸福,不过在他的理解中,我们却看不出任何纵欲主义的色彩。在伊壁鸠鲁看来,幸福就在于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这种关于幸福的定义当然很消极,他是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来界定幸福的,他并不说幸福是什么,而是说幸福不是什么。只要身体上无痛苦,灵魂上无纷扰,这就是幸福了。
伊壁鸠鲁认为,要达到身体上的无痛苦,就要求我们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不要暴饮暴食,而是采取劳逸适度的生活态度。但是,我们在世间感受得更加深刻的还不在于身体上的痛苦,而在于灵魂上的纷扰。
伊壁鸠鲁认为,导致我们心灵产生纷扰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对自然中的各种异象感到恐惧,面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山崩海啸,我们感到大惑不解,我们总以为是神造成了这些奇异的自然现象,所以在心理上对神产生了一种畏惧之情。这种对神的畏惧,对自然异象的不解,是造成我们灵魂纷扰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对死亡的恐惧,人生在世,谁不畏死?这种对死亡的恐惧,很多哲人都讨论过,死亡是哲学关注的一个永恒主题。我常常说,对死亡的恐惧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根源,生活中的任何苦恼都有解决的办法,唯独死亡所引起的苦恼是没办法解决的,因为谁都不可能逃避死亡。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对死亡的苦恼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苦恼,它是在经验世界无法解决的。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健康地生活着,但是对死亡的恐惧却时常萦绕着我们,使我们的心灵遭受苦恼的折磨。第三个原因,就是与他人的不和。大家都知道,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常常也是引起灵魂纷扰的一个重要原因。伊壁鸠鲁对于导致灵魂纷扰的三个原因的总结是非常有道理的,在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这三个原因确实是引起人们精神烦恼的重要因素。
针对这三个原因,伊壁鸠鲁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面对着那些自然的异象,如电闪雷鸣、山崩海啸等,人们通常以为是自己得罪了神灵,致使神灵发怒了。而伊壁鸠鲁却是一个原子论者,他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思想,试图用原子论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告诉人们,这个世界说到底就是由一大堆原子组合而成的。他并不否认神的存在,但却认为神只是存在于原子所构成的不同世界的缝隙之中,神从来不干预原子构成的世界。既然神不干预原子构成的世界,那么在世界里面的一切自然现象,如电闪雷鸣、山崩海啸等,都有其自然的原因,与神的喜怒哀乐不相干。因此,我们对于神灵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伊壁鸠鲁是一个原子论者,但是他对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有两点发展:第一,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和原子之间没有性质上的差别,只有形状、排列方式方面的差别。但是伊壁鸠鲁又增加了一点,他认为原子除了形状和排列方式的差别之外,还有重量上的差别,正是重量上的差别使得原子在空中做各种不同的直线运动或偏斜运动。原子在虚空中的运动,受其重量的影响,原子的重量不一样,它们的运动速度也不一样。
第二,德谟克利特由于过分强调必然性,所以在他的原子世界里只有直线运动。伊壁鸠鲁却认为,原子不只是在虚空中做直线运动,而且原子运动的轨迹可以发生偏斜。
当一个原子可能做直线运动,也可能发生偏斜时,偶然性就出现了。而在这种偶然性背后,潜藏着一种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自由意志。原子为什么会发生偏斜?因为它是自由的,它可以自由地决定自己运动的轨道。这样一来,就把自由赋予了原子世界,从而突破了德谟克利特原子世界中的那种铁一般严格的必然性。
当然,伊壁鸠鲁本人主要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他只是想要说明,在一个充满了偶然性的自然世界中,一切事物都是变化无常的,这些变化与神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大家不必因此而惊慌失措。
对死亡的恐惧是引起灵魂纷扰的第二个原因,对此,伊壁鸠鲁却认为,死亡并不足以恐惧,他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认识论上,伊壁鸠鲁也不同于德谟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在认识论上是一个唯理论者,他把通过感官而获得的知识称为“暧昧性的认识”,只有理性思维对于原子和虚空的认识才是“真理性的认识”。但是伊壁鸠鲁却认为感觉才是最可靠的,感觉是真理的来源。
伊壁鸠鲁认为,人活着的时候,从来没有感觉到死亡;而人一旦死了,就消散为一堆原子(按照原子论的观点,人也是由原子构成的,所以死了就意味着人消散为一堆原子),因此也就对死亡没有任何感觉。既然人活着的时候感觉不到死亡,死了以后又没有任何感觉,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对死亡感到恐惧呢?因此,无论是活着还是死了,我们都没有必要恐惧死亡。
引起灵魂纷扰的第三个原因是人际关系的不和。对此,伊壁鸠鲁认为,这个问题更容易解决了。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伊壁鸠鲁主张构建一个和谐社会来消除人际关系的不和。
伊壁鸠鲁认为是通过社会契约建立的,伊壁鸠鲁是继普罗泰戈拉之后再次明确表述了社会契约论思想的哲学家。他认为,如果人们通过一种契约来建立社会,大家都按照契约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人们之间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人际麻烦了,人际关系也就和谐了。退而论之,如果这个方案解决不了问题,大家都不遵守契约,那么我至少还可以退出这个社会,独善其身。我可以保持自己心灵的自由,潜心地研究自己的哲学,与世隔绝,这样也可以避免与他人之间的纠纷。
伊壁鸠鲁的弟子们把伊壁鸠鲁伦理学概括为医治心灵的“四药方”,那就是“神不足惧,死不足忧,乐于行善,安于忍恶”。
和伊壁鸠鲁主义一样,斯多葛主义也是产生于希腊化时代、后来流行于罗马世界的一个哲学流派。斯多葛学派可以分为早期斯多葛学派和晚期斯多葛学派,早期最初的创始人名叫芝诺,但是不要与那位诡辩论者芝诺相混淆,而是另一位出生于塞浦路斯岛的芝诺(Zeno,约前334—约前262)。
芝诺以及早期斯多葛学派所关心的问题与伊壁鸠鲁主义相同,都是要探讨如何追求心灵的宁静,以一种不动心的态度来面对世界上的纷扰万象。但是,斯多葛主义者所主张的具体路径与伊壁鸠鲁主义者不同,他们的观点似乎更加消沉一些。
相比之下,早期斯多葛学派比晚期斯多葛学派更加理智一些,对于生活的拒绝或者在禁欲主义方面也不是走得那么远;但是晚期斯多葛学派就完全走向了禁欲主义的极端,从而最终形成了与伊壁鸠鲁主义针锋相对的一种思想潮流。
人在面对命运时,不要去抗争,不要去反抗,而应该逆来顺受,这才是保持心灵平静或不动心的灵丹妙药。反之,人越是与生活相抗争,他就会越痛苦。无论是残酷的命运,还是通达的命运,人都应该坦然处之,这样他才能真正地获得自由。
斯多葛学派认为,命运是逻各斯,而逻各斯就是世界理性,就是世界的本质或形式,即普遍必然性的客观规律。面对着这种世界理性或规律,我们只能认识它、遵循它、按照它来办事,这就叫作自由。
斯多葛学派认为,一个人顺应自然、服从命运,这就是道德的生活,而道德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斯多葛主义和伊壁鸠鲁主义一样,都追求幸福,但是他们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伊壁鸠鲁主义把幸福理解为快乐,快乐即幸福。虽然伊壁鸠鲁本人与他的继承者们对于快乐的理解是不同的——伊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身体无痛苦和灵魂无纷扰,而他的继承者们却逐渐把快乐演变为一种放浪形骸的纵欲主义——但是总的来说,伊壁鸠鲁主义认为快乐即幸福。斯多葛主义者也追求幸福,但是他们却反对快乐即幸福的观点。那么,斯多葛主义者认为什么是幸福呢?他们主张,美德即幸福。由此可见斯多葛主义与伊壁鸠鲁主义之间的差别,它们二者,一个把美德等同于幸福,一个把快乐等同于幸福,这样就导致了美德与快乐之间的对立。
由于西塞罗的中介作用,斯多葛主义在罗马世界开始广泛流传,尤其是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当踌躇满志、以世界主人自居的罗马人在源源不断的外省财富和东方享乐主义的腐蚀下日益颓丧堕落下去的时候,作为一种回应姿势,斯多葛主义的观点也变得越来越偏激,消极避世的色彩也越来越显著。我们把这一时期的斯多葛主义归入晚期斯多葛学派,它的主要代表是三位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一位是罗马大臣塞涅卡,一位是获释的奴隶爱比克泰德,还有一位是罗马皇帝奥勒留。他们三个人的基本观点都是主张服从命运,只不过一个比一个更加悲观、更加沮丧。
面对着这样一种堕落,斯多葛主义者仍然坚持美德,但他们又没办法改变这个社会,于是就只能在哀叹之余采取洁身自好的避世态度,从而把早期斯多葛主义的美德观推向了一种极端的消极状态。这种极端的消极状态既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彻底唾弃,同时也就把希望指向了另一个世界。这样一来,晚期斯多葛主义的避世主义就与早期基督教的天国理想联系起来。
塞涅卡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始终都是被命运所控制的,命运就是神的意志的体现,因此服从神的意志就是自由。他有一句名言:“愿意的被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被命运拖着走。”不管你愿不愿意,反正你最终都得跟着命运走。如果你愿意,就是说你认识到了神的意志和命运,你就会顺应命运而行,这就叫作自由;反之,如果你不认识命运,到头来就只能被命运硬拖着向前走,这是一种悲惨的状况。
爱比克泰德由于是奴隶出身,经历过很悲惨的生活,所以养成了一种坚忍的精神,能够忍受各种痛苦。安于忍恶,这本来也是伊壁鸠鲁主义的观点,晚期斯多葛主义者却把它发展到极致。爱比克泰德认为,人应该学会忍受各种苦难,即使是面对一个罪恶的世界,也不要去反抗,而应坚定不移地服从命运的安排。他大力宣扬一种宿命论,认为人生的一切兴衰泰否、悲欢离合都是命运注定的,人不要去做徒劳的反抗。当我们面对各种灾难的时候,应该懂得,使我们恐惧的不是灾难本身,而是我们对待灾难的态度。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在灾难面前感到恐惧了。他认为,如果一个人面对灾难而怨天尤人,那么这说明他完全没有教养;如果他面对苦难时并不怨天尤人,只是责怪自己,那么这说明他已经开始进入教养的状态;如果他面对苦难时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责怪自己,而是完全听天由命,坦然处之,那么这说明他已经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
爱比克泰德的另一个著名观点是,人生在世就如同演员在戏台上一样,一切剧情早已被导演规定好了,这人生的导演就是无所不在的命运。一个人活得长还是活得短,活得好还是活得赖,这些早就被注定了。
第三位哲学家名叫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他是一个罗马皇帝,也是三位晚期斯多葛主义者中思想最消沉的人。奥勒留的特点是,以位极至尊的皇帝身份,用极其优美的文笔,表述了对人生极度悲观的态度。
奥勒留的悲观主义源于他把世间一切都看透了。在他眼里,人不过是浩渺苍穹之间一小点微不足道的尘埃,时流忘川之中的一个转瞬即逝的可怜虫。宇宙在时间上是延绵无尽的,在空间上是浩瀚无边的,而我们每个人却在如此广阔的空间和如此漫长的时间的交汇点上偶然地出现了,因此生存不过就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情。如果这样想一想,我们自然就会看破红尘,窥透人生,世间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抛弃?还有什么功名利禄值得去为之奋斗?还有什么悲哀苦楚不可以超脱?既然人生在世不过就是时空交汇的一瞬间,那么一切试图改变命运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就如同蚍蜉撼树、螳臂挡车,不过是痴心妄想罢了。另一方面,奥勒留又极力强调宇宙各环节之间的普遍联系,任何一个环节遭到了破坏,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从而扰乱整个宇宙的秩序。因此,我们既不可能反抗命运,也不应该反抗命运,一切都应顺其自然,安于现状。
皮浪继承了普罗泰戈拉的观点,认为任何理论都有相反的说法,所以如果你对一件事情说是,别人肯定也可以说不。
皮浪指出,我们的灵魂为什么老是不得安宁?就是因为我们老是喜欢做判断,而当我们的判断与别人的观点处于对立状态时,当我们发现有人反对我们的观点时,我们就会陷入混乱和苦恼之中。可见,我们苦恼的根源,就在于我们太爱做判断;而要想避免苦恼,获得心灵的安宁,就应该对任何事情都采取不做决定、悬置判断的态度。
皮浪的怀疑主义比后世的怀疑主义更加彻底的地方,就在于他不仅在理论上进行怀疑,而且在行为上身体力行。
当然,在晚期怀疑主义者的这些论式中,尤其是在十个老论式中,难免有以偏概全、混淆视听之嫌,利用某些感觉的相对性来否定一切感性知识的有效性。但是,他们关于理论矛盾的观点却是非常高明的,有些看法实际上已经触及极其艰深的逻辑悖论和公理系统问题,这些思想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当然,怀疑主义者根据这些论式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的有效性,这个结论是有问题的,而且也违背了他们不做判断的基本立场,因为断定知识是无效的,这本身也是一种判断。由此看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完全悬置判断,因为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决定,即决定不做决定。
罗马帝国时期的哲学过渡形态
希腊化时代的三大学派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时期,其中的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葛主义构成了贯穿于整个罗马帝国的两个最主要的思想学派。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希腊哲学正在发生一种转变,即从追问本原、实在等背后的东西转向了关注当下呈现的人生感受,从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转向了人生哲学和伦理学。哲学不再关心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是追问生存的意义是什么。这种生存论的转向就直接导出了后来的基督教哲学。
基督教的上帝与希腊哲学的世界本原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联系在于,二者都是现象世界背后的东西,都是起决定作用的终极实体。那么它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就在于基督教的上帝与人的生存状况直接相关,而希腊哲学所追寻的那些本原,无论是原子还是理念,都与我们的生存状况漠不相关。
到了19世纪,当一些理性主义的思想家开始批判地考察基督教时,他们又公然主张,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不是有什么样的上帝就会有什么样的人,而是恰恰相反,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帝。上帝只不过是人类自身本质的抽象化,然后人类把这个抽象的本质客观化、对象化,再对它进行顶礼膜拜。这就是19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费尔巴哈关于宗教异化的观点。无论是按照《圣经》的说法,还是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上帝作为万物的本原都不同于希腊哲学的那些本原,他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实体,而是一个客观化了的主观精神,是人的本质的一种客观化或异化。
我们每个人在儿童时期首先关注的是对象,而不是自身,当你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是你眼前呈现出来的世界,而不是你自己。然后当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反过来认识我们自身,才开始有了自我意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升和转折。再往后,我们就开始考虑自我与对象的关系,开始反思在自我意识中呈现出来的客观世界,从而形成一种关于世界与自我之关系的意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个体意识的发展过程与哲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个体发生学与种类发生学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
如果说希腊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一种自觉的方式创立了形而上学,那么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主要贡献就在于以一种自在的方式表述了自我意识,而希腊化时代的三大学派则构成了二者之间过渡的一个必要中介。
斐洛(Philo,约前20—约50)是生活在公元之交的希腊化时代的一个犹太人,他主要生活在当时希腊化世界的中心,即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斐洛用希腊哲学的“逻各斯”和“理念”来说明上帝与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的联系,他像柏拉图一样认为,上帝的“逻各斯”或“理念”构成了世界的本原,而感性世界只是“理念”的摹本,上帝是通过“逻各斯”或“理念”来创造世界的。这种观点为基督教的“道成肉身”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因此恩格斯把斐洛称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
斐洛虽然试图用柏拉图哲学来解释犹太教经典,但是严格地说来他还不能被称为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而只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一个思想先驱。真正堪称新柏图主义者之典范的人物是生活在公元3世纪的普罗提诺(Plotinus,约204—270),罗素把他称为“古代伟大哲学家中的最后一个人”。
普罗提诺是一个新柏拉图主义者,那么他与柏拉图的最大不同之处在哪里呢?就在于他把柏拉图哲学神秘化了。柏拉图哲学相比起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说,本来就已经够神秘的了。我们曾经讲过,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了一种审慎的理性,柏拉图主义则代表了一种神秘的狂热。但是相对而言,普罗提诺的观点就更加神秘了,他提出了一种哲学的“三位一体”。
普罗提诺的第一个概念叫作“太一”,他认为世界最初就是太一,太一到底是什么呢?这很难说清楚。大家可以把它想象为柏拉图的“善”的理念,也可以把它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但是它似乎又不像这些最高的东西那样明晰,而是处于扑朔迷离之中。总而言之,太一是最原始的世界本原,万物都是从它里面产生出来的。我们既不能解释它的原因,也无法解释它到底是什么,对于太一,我们什么也不能说。普罗提诺强调,太一既不是有限的,也不是无限的;既不是一,也不是多;既不运动,也不静止。对于这样一个东西,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因为它把矛盾的两个方面都否定掉了。
普罗提诺的第二个概念叫作“努斯”,这是从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那里借鉴来的概念。普罗提诺认为,努斯就是具体化的太一。太一是无法限定和无法表述的,但是它总得在时空之中有所呈现,而这种呈现或具体化就是努斯。用普罗提诺自己的比喻来说,太一和努斯的关系就像太阳和太阳光的关系一样,我们正是通过太阳光才能见到太阳,没有太阳光,我们就见不到太阳。同样地,太一是我们无法认识的,我们却可以认识努斯,并且通过努斯而窥见太一。但是另一方面,太阳和太阳光并不是两个东西,而是同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而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差别。所以说,努斯就是太一的具体化,就是呈现为一的太一。
“努斯”是太一的具体化,而它的进一步分化就导致了第三个概念“灵魂”。如果说努斯是呈现为一的太一,那么灵魂就是呈现为多的太一,它们居住在我们的肉体之中,通过努斯与太一相联系。灵魂是多,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个灵魂。然后灵魂再创造出肉体,或者说灵魂进入肉体,使肉体获得生命,这就是柏拉图的观点了。灵魂是带着努斯所体现的太一理念而进入肉体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部分地窥见到太一。如此一来,太一、努斯、灵魂这三个概念就构成了一种辩证的关系——太一通过努斯(一)而分化为灵魂(多),居住在我们的肉体之中,众多的灵魂通过对唯一无二的努斯的认识而窥见那个不可认识的太一。
这样一种神秘主义的哲学观点,与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理论是完全同构的,我们只需要改换一下名称,把太一称为圣父,把努斯称为圣子,把灵魂称为圣灵,普罗提诺的哲学“三位一体”就变成了基督教的神学“三位一体”。
我们最后介绍的一位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家,就是普罗提诺的学生波菲利(Porphyry,约234—约305)。波菲利本人在哲学上并没有太多的建树,他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哲学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范畴篇》进行了一些解释,从而为后世留下了一些颇费争议的问题。
共相就是一般的东西,就是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柏拉图的理念就是一个共相。共相是相对于殊相而言的,殊相是指事物的具体现象,而共相则是指事物的普遍本质,比如我们说人是可以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理性动物,这就是关于人的一个共相。每一类事物之所以为该类事物,都是因为它们有某种共同的东西,猫与狗的差别,就在于它们有不同的共相。所以共相就是事物的普遍本质,它决定了一个事物之为这个事物的根据。
关于共相的这三个问题是这样表述的:第一,共相(或种与属)究竟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还是仅仅存在于思想之中的一个抽象概念?第二,如果它们是实体,那么它们究竟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第三,如果它们是无形的,那么它们究竟是与可感事物相分离的,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这些问题都是非常费解的,它们不仅涉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可知论和怀疑论等各种不同的立场,而且其中的奥妙之处极其深远绵长,决非一个简单的陈述句可以回答得了的。
根据对于共相的不同看法,中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划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实在论,另一个是唯名论。
![图片[1]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哲学】《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个人摘录(第六讲 希腊哲学的衰颓)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小竹の笔记本](https://img.smallbamboo.cn/i/2025/09/18/68cba8e7b2b8d.jpg)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662629/
说明:本文每一行均为部分摘录,阅读连贯性可能较差,个人存档用,推荐购买正版书籍阅读。
2. 论文总结类文章中涉及的图表、数据等素材,版权归原出版商及论文作者所有,仅为学术交流目的引用;若相关权利人认为存在侵权,请联系本网站删除,联系方式:i@smallbamboo.cn。
3. 违反上述声明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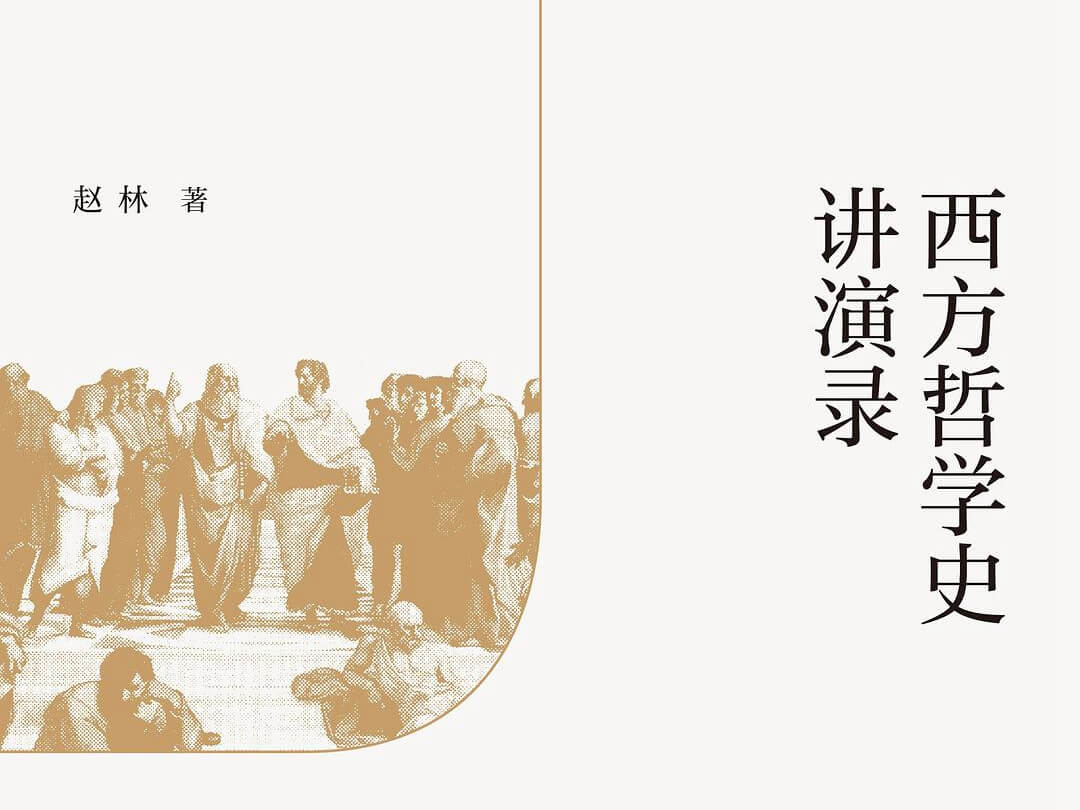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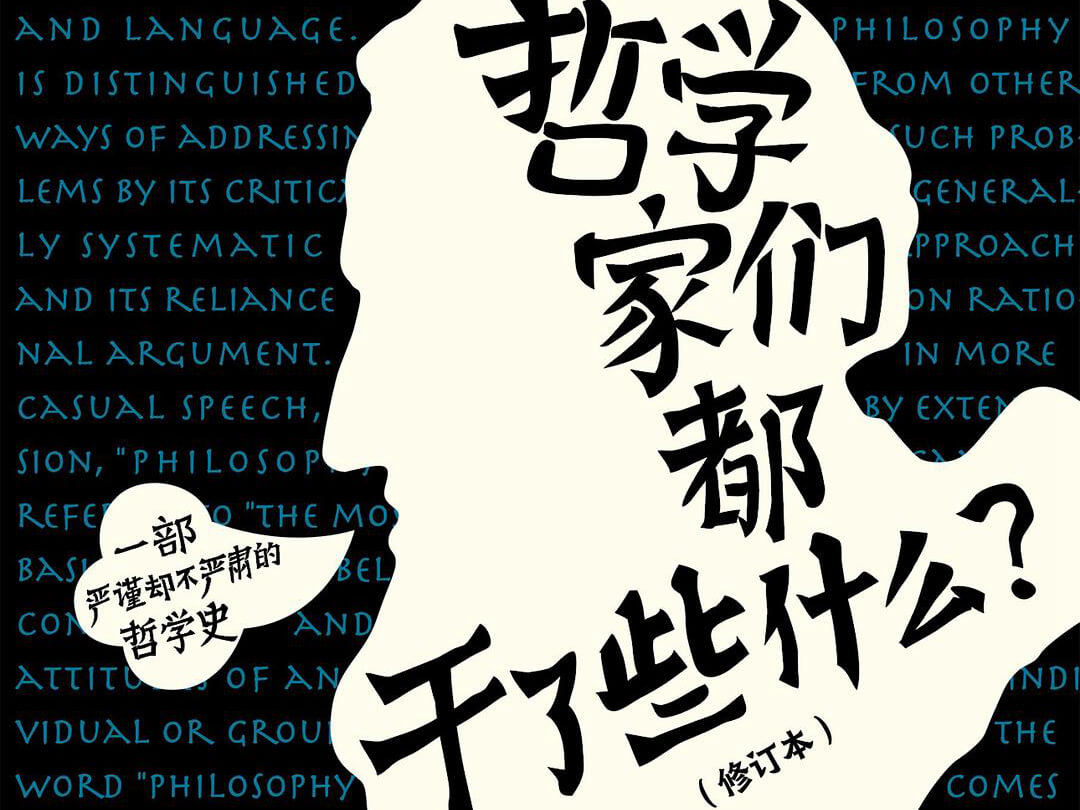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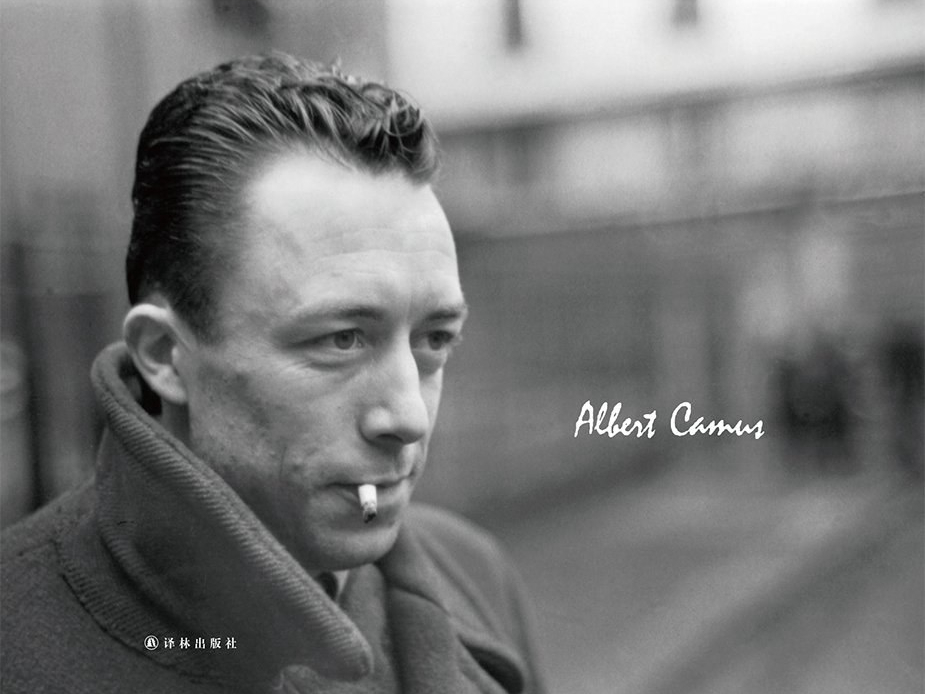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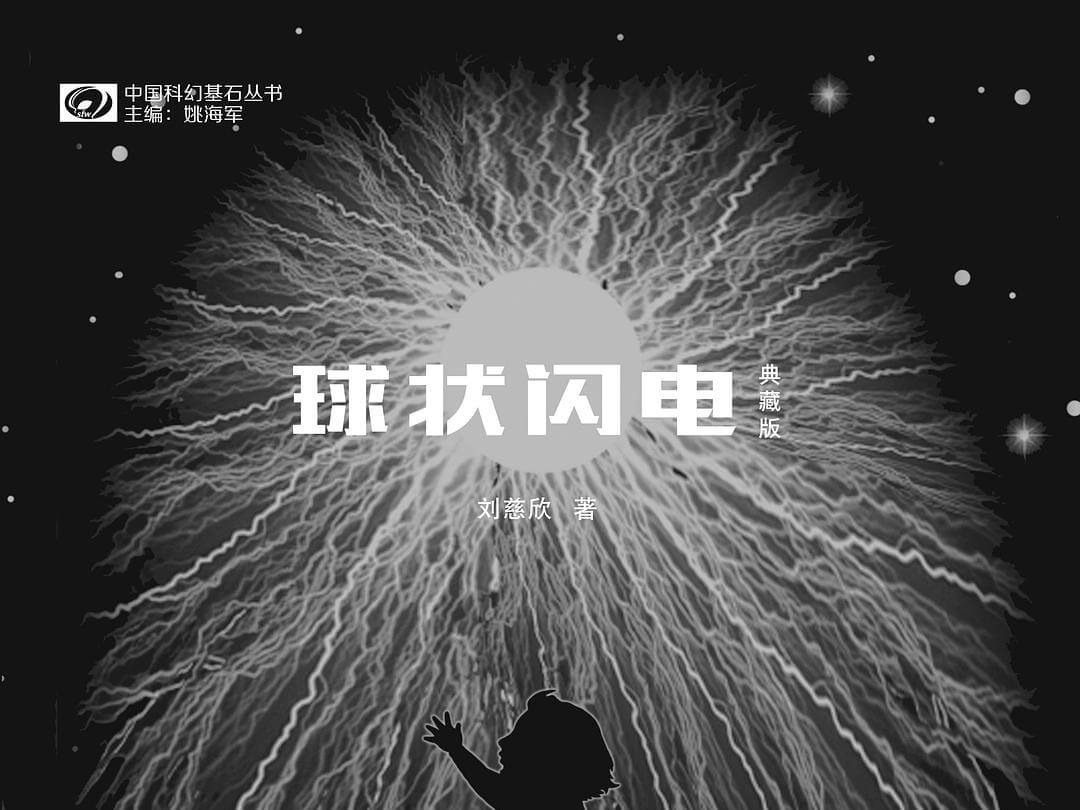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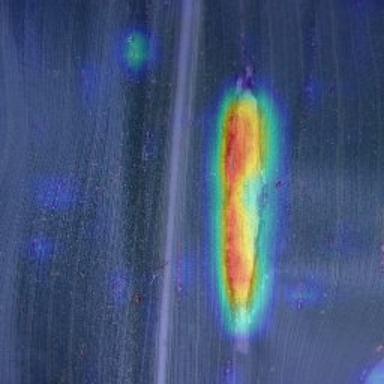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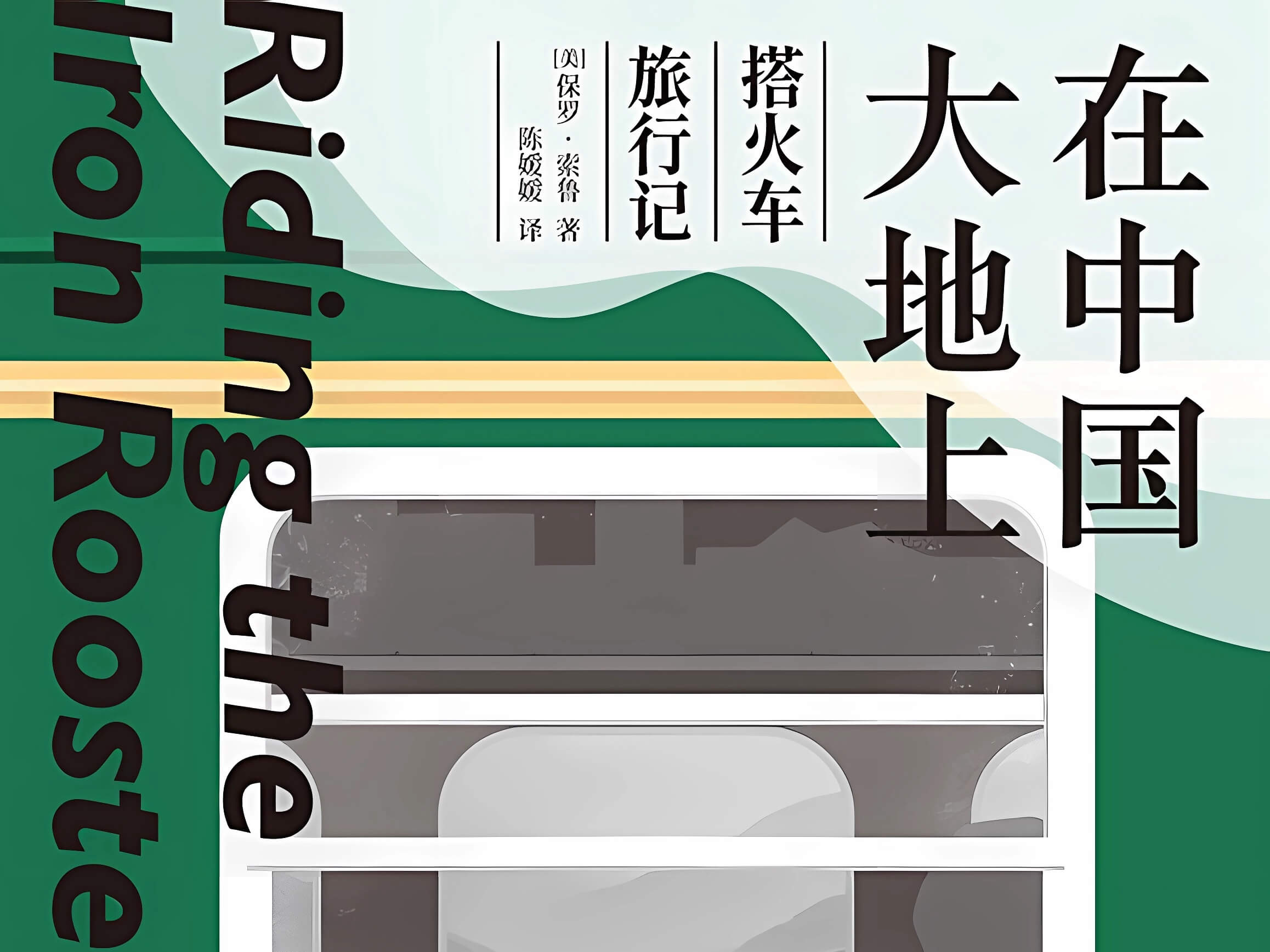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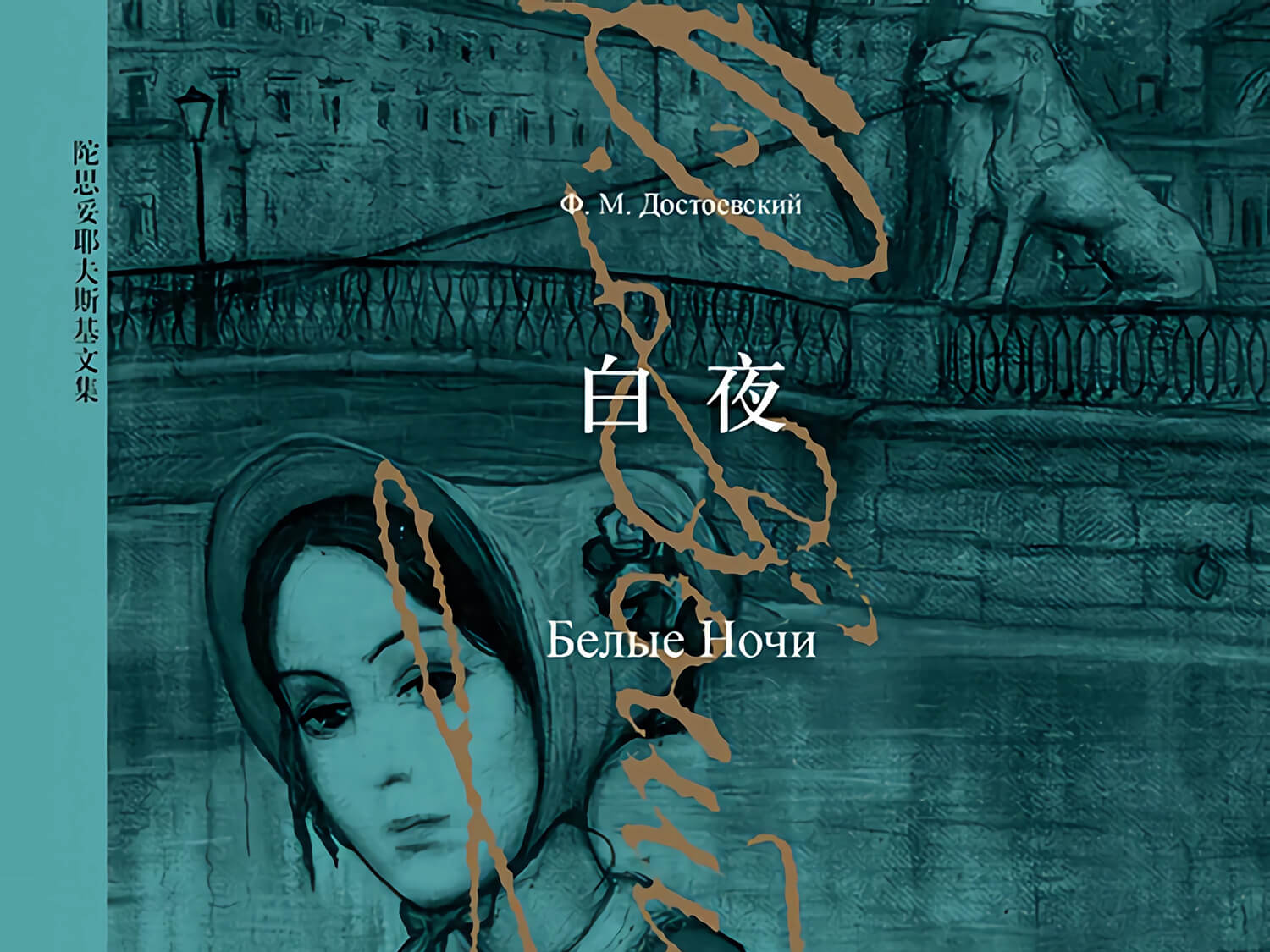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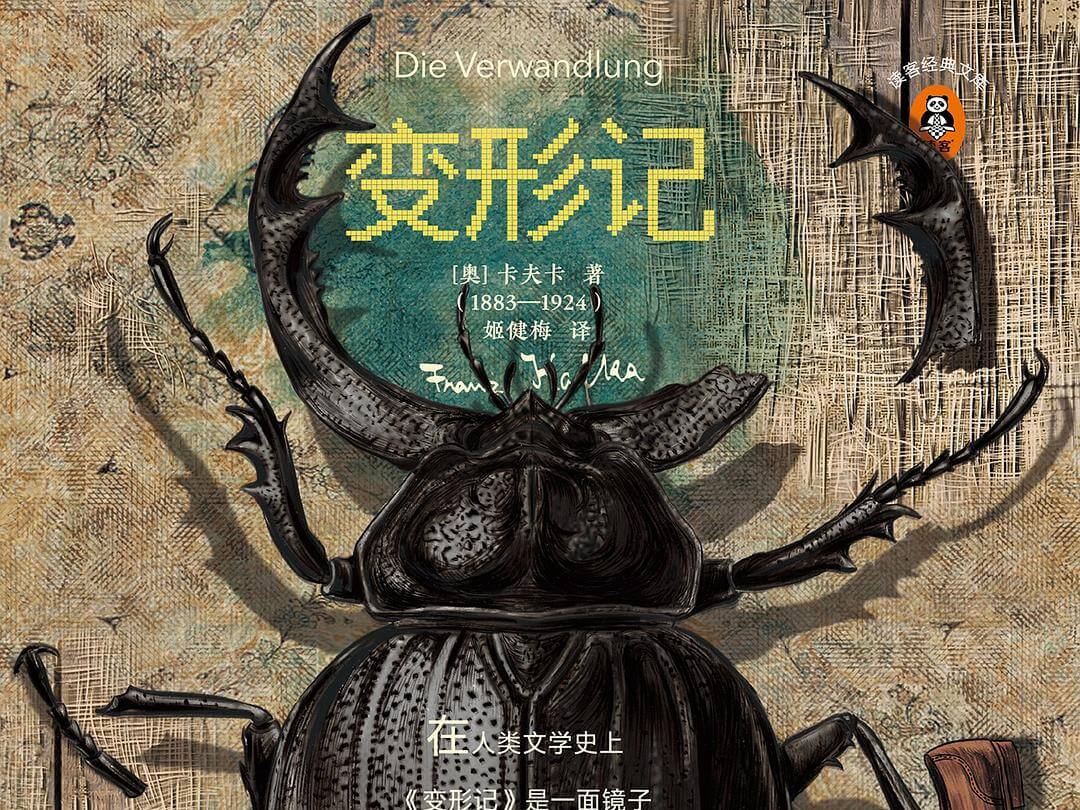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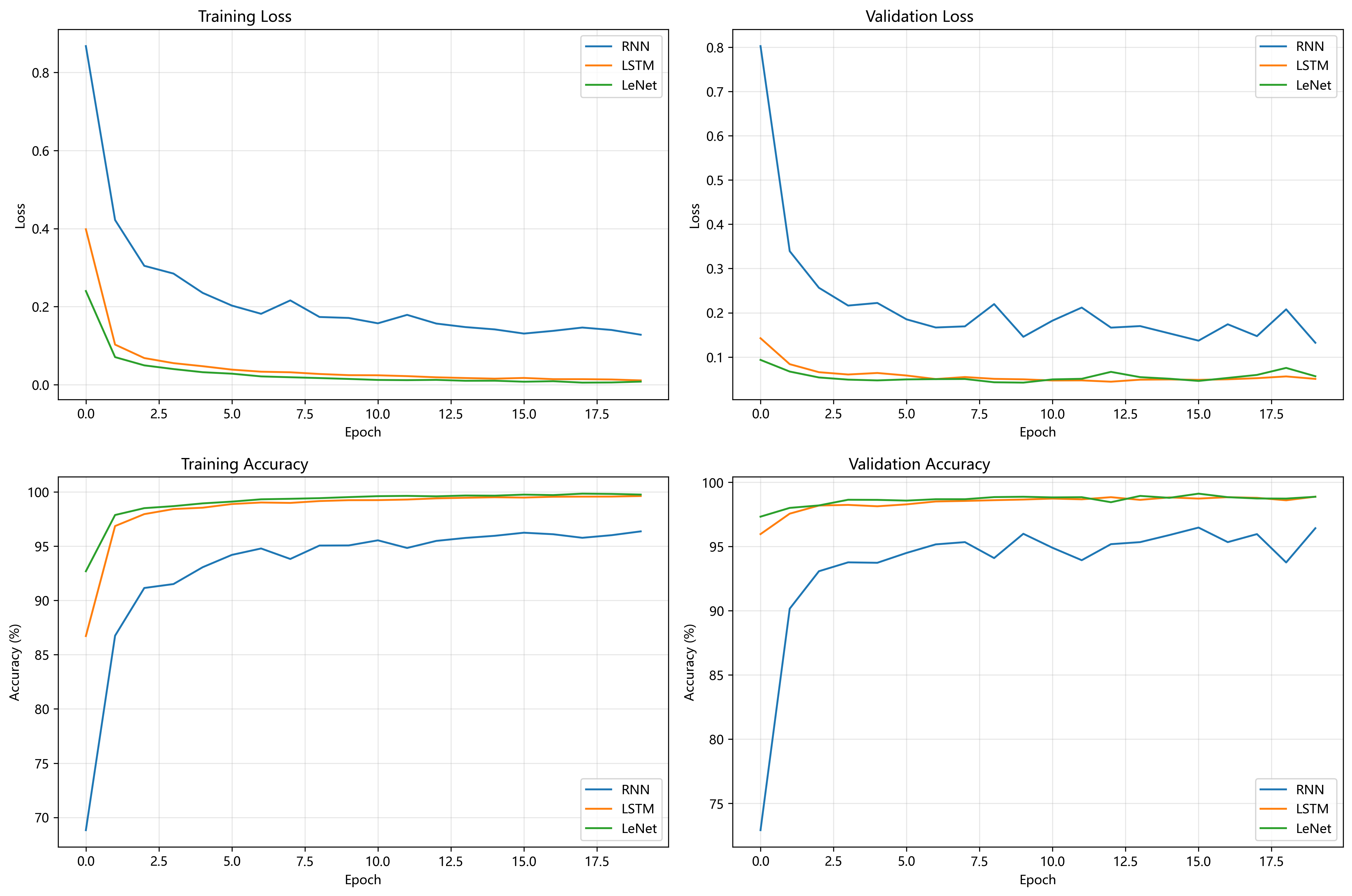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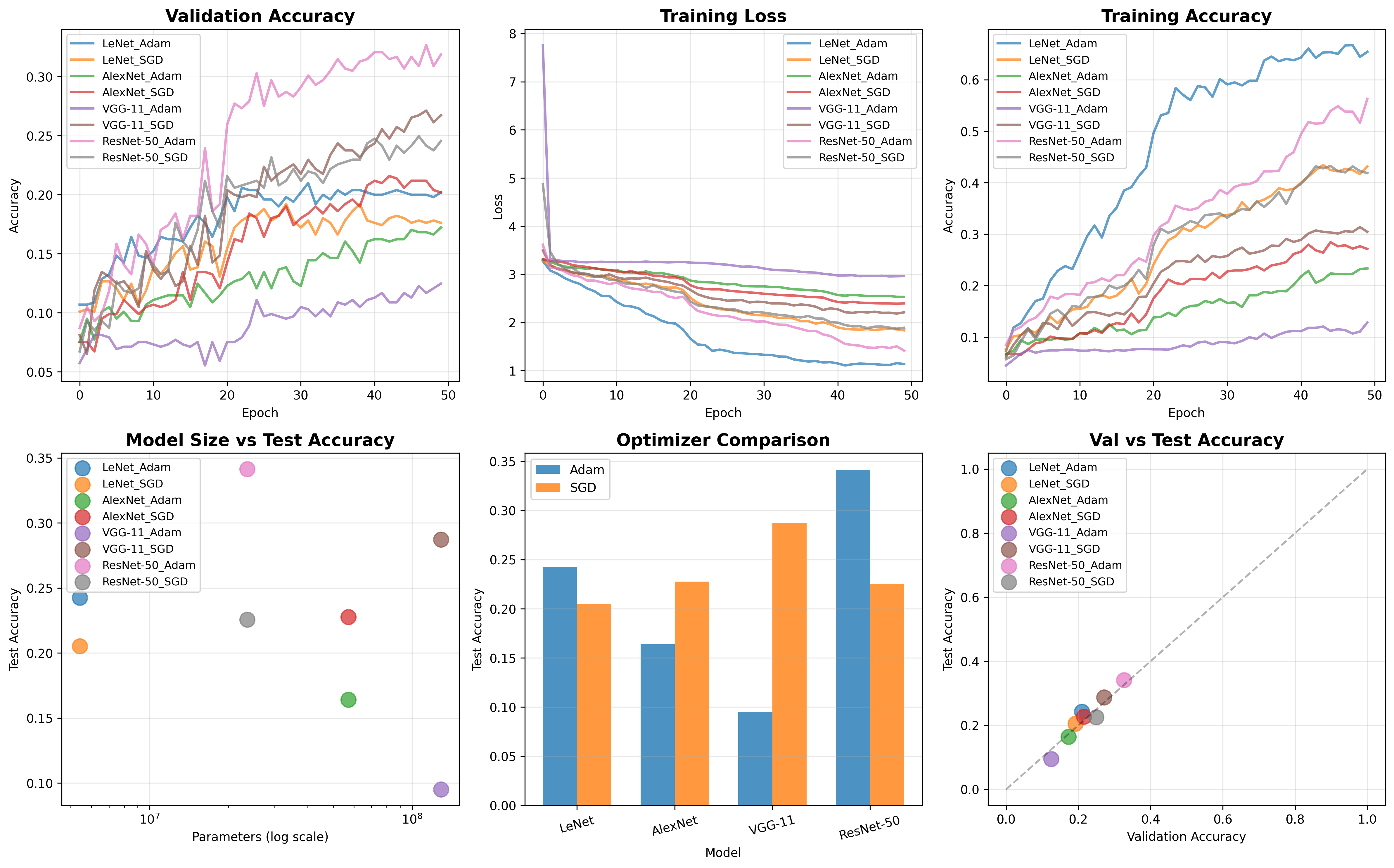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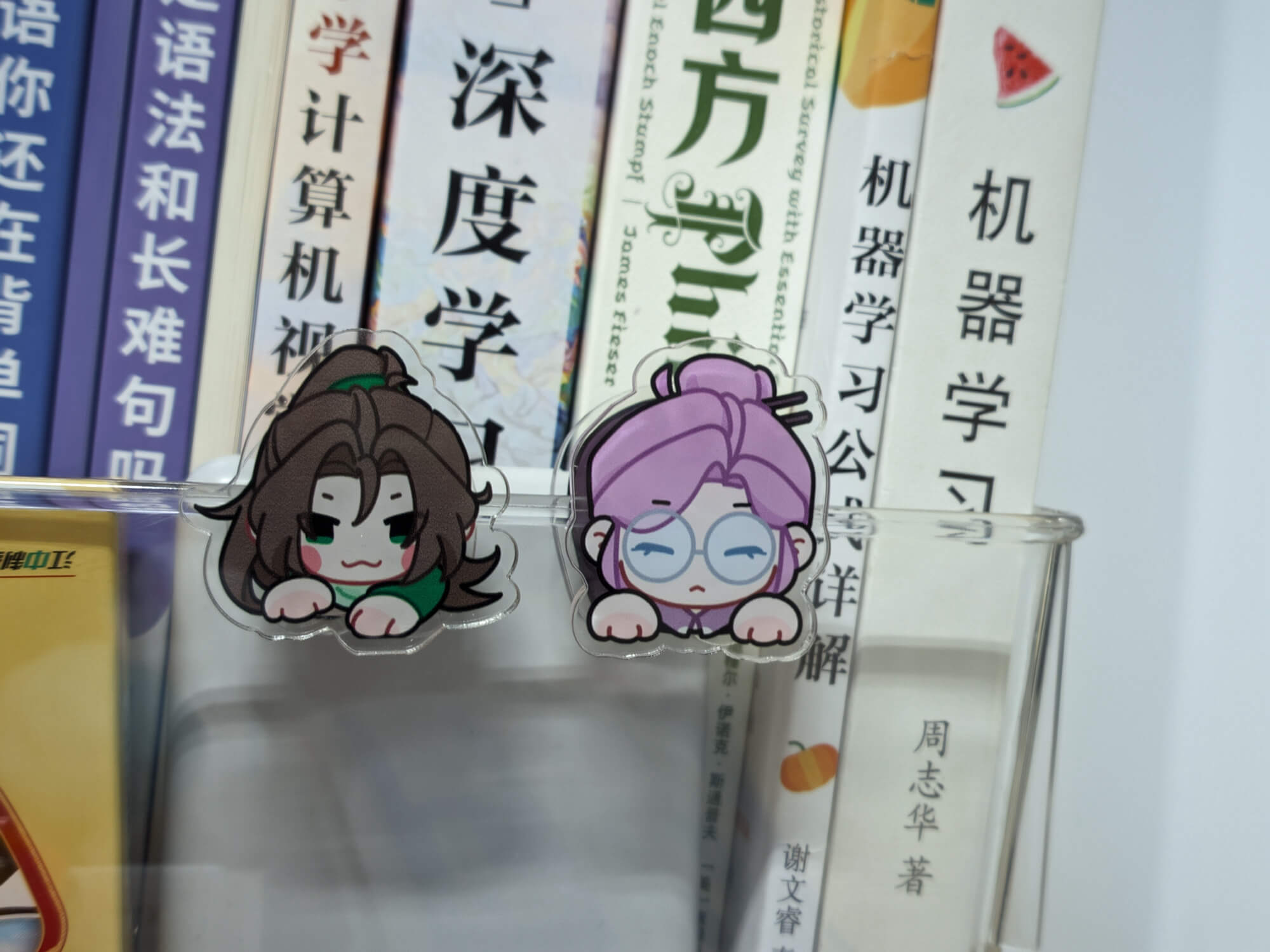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