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为了突出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思想发展脉络,我们以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作为一条主线,围绕着这条主线来讲解基督教哲学。
教父哲学
我们今天的人之所以很难理解基督教信仰,是因为我们生长在一种理性主义氛围中,我们老是喜欢用理性的标准来考察基督教。
20世纪的一位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经说过:“正是因为生活中充满了绝望,我们才被赋予了希望。”在罗马帝国时期,基督徒们生活在一种完全绝望的境遇中,正是这种绝望的现实状况,使他们对彼岸世界充满了强烈的希望。这种对于彼岸世界的强烈希望,就表现为关于上帝恩典和死而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在那样的处境下,一种坚定的信仰胜过了所有的辩证法和理性知识。对于一个生活在苦难处境中并且有着坚定信仰的基督徒来说,希腊式的理性和辩证法只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无聊玩意儿,那是分文不值的。况且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东西,而信仰的对象却是超出人之上的,是上帝的奥秘。面对着上帝的奥秘,人的理性又算什么?因此,早期基督教神学充满了超理性的信仰色彩。
一个怀疑主义者与一个基督徒,在关于上帝的问题上是无法进行讨论的,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理性处理的范围。
在基督教中,骄傲和狂妄乃是罪恶的根源,亚当、夏娃最初就是因为骄傲、不听上帝的教导,才犯下了原罪。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理性不仅不能取代信仰的重要地位,而且甚至有可能成为罪恶的根源。因此,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圣灵的感动往往要比任何逻辑推理都更加具有说服力。
这种超理性或反理性的信仰特点,构成了基督教最初的理论形态——教父哲学的思想基调。
基督教是一种高级宗教,它有着一套成熟的思想体系,这套思想体系不能仅仅建立在单纯的信仰之上,还必须要有博大精深的理论根基。这就是成熟形态的基督教神学,在中世纪表现为烦琐晦涩的经院哲学。
然而,理性一旦被广泛地运用,它就很可能会对信仰产生一种冲击作用,因为许多信仰的东西是经不起理性推敲的。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仅相信基督教的教义,而且寻求进一步去理解这些教义,那么一方面我们固然可以说他更富于理性精神了,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很可能会背离虔诚的信仰。
那个在经院哲学中小心翼翼地为神学教义寻求论证的理性,最终竟在18世纪启蒙运动中发展成为对宗教信仰进行猛烈批判的无情杀手!
教父哲学一般的倾向是用信仰来排斥理性,只要信仰不要理性;稍微宽容一点的教父则主张,在信仰的前提下寻求理解,先信仰后理解。因此,教父哲学的总的特点是,信仰排斥或者超越理性。
教父时代开始于公元1世纪末叶,结束于公元10世纪,这个历史跨度非常大,经过了罗马帝国时期和中世纪早期这两个时代。
从公元1世纪末到公元5世纪,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教父不仅有着坚定的信仰和崇高的牺牲精神,而且具有深厚的知识素养,其道德文章均堪称上乘。
到了公元11世纪以后,随着西欧社会逐渐从蛮族大入侵的严重后遗症中复苏,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强(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亚里士多德主义重新流回西欧社会),基督教世界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文化复兴的浪潮,大学也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于是一个新兴的哲学流派——经院哲学也就应运而生,成为中世纪后期的主要哲学形态。
早期教父的历史使命既然是要把希腊文化素养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用前者来论证和强化后者,那么如何实现二者的结合,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基督教信仰与希腊罗马文化在整个价值取向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二者一个是悲观主义的,一个乐观主义的;一个是唯灵主义的,一个是物质主义的;一个是禁欲主义的,一个是纵欲主义的,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是迥然而异的。
在这种情况下,教父们往往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深厚的希腊文化素养使得他们想把基督教信仰奠定在博大精深的希腊哲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基督徒身份又使他们必须承担起用信仰来抵御各种希腊世俗知识的神圣使命。因此,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只能以一种矛盾的态度来处理希腊哲学。虽然他们常常无意识地用希腊哲学思想来论证和充实基督教信仰,但是在意识层面上,他们却始终要保持一种反对希腊异教知识的姿态。正是这种尴尬的状况,造成了早期教父哲学用信仰来贬抑理性的基本倾向。
相比而言,希腊教父要比拉丁教父更加尊重希腊哲学,更加富于理性精神,力图把希腊哲学与基督教信仰结合起来;而拉丁教父则更加狂热,对待希腊哲学和理性的态度也更加极端,主张用基督教信仰来彻底取代和否定希腊哲学。
德尔图良有一句名言。在谈到“三位一体”神学教义的奥秘时,他明确地宣称:“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
上帝的儿子死了;正因为这是荒谬的,却无论如何是应该相信的。并且他被埋葬了,又复活了;正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这事实却是确凿的。
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是我们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这些超出理性范围的东西都是荒谬虚假的,我们应该经常对自己的理性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这就是“正因为其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所在。
以德尔图良为代表的拉丁教父表现了这样一种用信仰来排斥理性的倾向,这种倾向最终压倒了希腊教父的更富有理性化色彩的观点,成为早期教会的主流观点。
我们发现,在这四次大公会议上遭到谴责的异端观点,基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比较容易被理性所理解。相反,那些被确定为正统教义的观点,基本上都带有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扑朔迷离、模棱两可,理性根本就无法把握,确确实实是一些只可信仰、不可理解的奥秘。
早期基督教神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上帝论,探讨上帝的本性和特点;第二是基督论,探讨基督的本性和特点;第三是人性论,探讨人的本性和特点。关于上帝论,最后形成的正统观点是“三位一体”教义,该教义确定上帝具有一个实体和三个位格。
基督论的情况也是如此,基督论主要探讨基督耶稣到底是一个神,还是一个人?
最后是人性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涉及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他为基督教神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个人就是圣奥古斯丁。
基督教的人性论主要涉及原罪与救赎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我个人认为,它在理论上甚至比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教义更加重要,因为它直接涉及人的生存状态问题。虽然在基督教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上帝,万事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和决定的,但是上帝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他开天辟地,而在于他和基督耶稣的关系。
基督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他构成了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构成了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中保。他为我们昭示了死而复活的福音,成为灵魂得救的“初熟之果”,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所以,基督教主要是对于基督救赎的一种信仰,而基督救赎的重要性恰恰是因为亚当的堕落即原罪才得以彰显的。可见,人性论所讨论的原罪与救赎理论,就是直接从人的生存处境出发来思考我们与基督以及上帝的关系问题,因此它构成了基督教核心教义的核心。
如果说希腊哲学最核心的问题是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那么基督教神学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人如何能够从罪恶中获得救赎。
奥古斯丁(Augustinus,354—430)是基督教神学理论的重要台柱,他与13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一起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两位最杰出的思想家。但是他们两人却代表着基督教哲学的不同方向,一个明显具有柏拉图主义的神秘色彩,另一个则更多地具有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审慎特点。作为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虽然不像德尔图良等早期教父那样用信仰来排斥理性,但是却仍然坚持先信仰、后理解的立场,推崇一种超理性的信仰。
关于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我在这里只介绍最主要的观点,其一是关于上帝创世的思想,其二是关于原罪与救赎的理论。
作为一个教父神学家,奥古斯丁为基督教的这种凭空创世说进行了理论论证。他认为,上帝创造世界根本就不需要利用任何材料,也不需要借助任何工具,甚至连时间和空间都不需要,上帝完全是凭着自己的语言而创造世界的,世界万物都是“上帝言说”的结果,这就叫作“道成肉身”。“道”就是上帝的语言,就是逻各斯,“肉身”就是有形的世界万物,上帝用语言创造了整个世界。
奥古斯丁巧妙地借用了希腊哲学的思想,把柏拉图的理念说、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学说与基督教的创世信仰结合起来。他认为,上帝首先创造了无形的“种质”,然后再根据“种质”复制出有形的万物。“种质”体现在上帝的语言里,它与有形万物的关系就相当于柏拉图的理念与感性事物的关系一样。所以上帝说要有什么,结果就有了什么。奥古斯丁强调,上帝创造“种质”以及“种质”流溢出万物的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种质”只是在逻辑上而非在时间上优先于万物。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创世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圣经》里说上帝在六天之间创造世界万物,那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是为了让缺乏哲学教养的老百姓们容易理解,而事实上整个世界是上帝在一瞬间创造出来的。
奥古斯丁在论述创世说时还提出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思想,那就是关于时间的理解。他认为,时间和空间与万物一样,也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在上帝创世之前,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在他看来,时间并非某种与人无关的客观之物,而是事物在我们主观感受中呈现出来的一种顺序,是“流逝的事物留给心灵的印象之持续”。
奥古斯丁所理解的无限或永恒不在时间之中,它恰恰是对时间的一种根本超越——永恒不是在时间之中,而是在时间之上;而我们却往往把无限或永恒付诸于永不停息的时间流之中。
灵魂不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永恒,相反,它是超越了时间才进入永恒。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永远只有现在,这就叫永恒。
奥古斯丁对于基督教神学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关于原罪与救赎的思想。奥古斯丁一生都被罪恶问题所困扰,罪恶问题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早年他曾经信奉摩尼教,这种来自波斯的东方宗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世界有两个本原,一个是光明或善,一个是黑暗或恶。受这两个本原的影响,因此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善恶参半,既有善的成分,又有恶的因素。皈依基督教以后,奥古斯丁放弃了这种二元本体论的观点,改信基督教的一元本体论。上帝是世界万物的唯一创造者,他是至善的,所以世界从根本上是善的。但是世间为什么会有罪恶呢?奥古斯丁认为,那是由于人滥用了自由的结果。
希腊伦理学所关注的,不是自由,而是智慧、正义等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出的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构成了著名的希腊四德。在希腊的这些美德中,是没有自由的。希腊人之所以对自由概念不太在意,我想可能是由于他们本来就生活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中,所以他们对自由的要求并不是太迫切。
伊壁鸠鲁是这样来探讨这个问题的:神或者愿意消除罪恶却没有能力,或者能够消除罪恶却不愿意。如果是前者,那么神显然不是全能的;如果是后者,那么神显然不是全善的。第三种情况是,神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消除罪恶,那么他就根本配不上神的名称。因此,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那就是神既愿意也能够消除世间的罪恶,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世界上的罪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个著名的伊壁鸠鲁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基督教的神学家们。
在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与世间的罪恶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以解释的深刻矛盾。这个矛盾困扰着历代的思想家,而奥古斯丁也深受其累,终其一生来思考这个问题。
皈依基督教之后,奥古斯丁放弃了摩尼教的二元本体论,把上帝看作唯一的本体。上帝是至善,是唯一的本体,恶不具有本体性,恶不是本质,而是本质的缺乏,即善的缺乏。善的缺乏就是恶,这就是奥古斯丁对于恶的性质的解释。
但是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呢?他们违背上帝意志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在这里,奥古斯丁就引出了自由意志,用自由意志来说明罪恶的原因。他解释道,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万物中,只有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因此上帝最钟爱人,他赋予人一种特殊的禀赋,那就是自由。自然界的所有事物都必须遵循自然界的严格必然性而运行,唯独人具有自由的能力,可以决定自己的行为。奥古斯丁强调,上帝赋予人以自由是出于善意,自由本身也是善的,但是人却滥用了自由,做出了违背上帝意志的事情(偷食禁果),犯下了原罪。因此,虽然自由是来自上帝,但是滥用自由而犯罪的责任却不在于上帝,而在于亚当、夏娃本身。上帝把自由这种高贵的东西给予人,本来是希望人用它来从善的,但是人却偏要用它来作恶,所以罪恶的原因在于人而不在于上帝。
莱布尼茨认为,自由是世间最高贵的东西,上帝为了让人享有自由,宁愿冒着人滥用自由意志而犯罪的危险。康德则认为,自由之所以为自由,就在于它是对上帝的秩序的背离。如果人完全按照上帝的意志来行动,上帝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叫你干什么你就不干什么,那么人就没有自由可言了。从这种意义上说,自由的第一个表现一定就是对上帝意志的背叛,这种背叛对于上帝来说就是恶,因此自由最初是与恶联系在一起的。但是,正因为自由的第一个行为是背叛,是恶,所以它就可以继续对背叛进行背叛,可以弃恶从善,因此自由的本质就在于不断地否定现实状态、超出自身。这种不断地背叛、不断地自我否定的能力,就是自由的真正本质。
黑格尔认为,自由就是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意识,它首先就表现为人对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区别的意识。
黑格尔强调,人正是从背离上帝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成为人的,人由于原罪而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踏上了一条自我放逐的道路。伊甸园是什么地方?黑格尔直截了当地指出,伊甸园乃是只有禽兽才能滞留的地方,禽兽在伊甸园里赤身裸体,却没有羞耻感,这说明什么?说明禽兽是没有自我意识的。人最初也与禽兽一样,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所以人最初就待在伊甸园里。但是,知识之果却让人有了自我意识,使人意识到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区别,所以当上帝再到伊甸园的时候,人就躲在树林里面,并且用无花果的树叶遮住了自己的隐私之处。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上帝是不同的存在者,自己与上帝是有差别的。
奥古斯丁认为,罪恶最初就是由于人不听上帝的话,滥用了自由意志。所以,罪恶既不是上帝造成的,也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人滥用自由意志的结果。他一再强调,自由意志本身是一个好东西,但是人却滥用了它,导致了罪恶。
晚年的奥古斯丁针对佩拉纠的自由意志论,提出了著名的预定论。佩拉纠(Pelagius,约390—418)是来自不列颠的修道士,后来到北非地区传教,他的神学思想影响了许多人,形成了一个佩拉纠学派。佩拉纠的自由意志论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要点:第一,亚当、夏娃所犯的罪与我们无关,他们只是为我们做了一个坏榜样,但是并没有败坏我们的本性。我们所犯的罪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并不能归咎于亚当和夏娃。第二,尽管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犯过一些罪,但是从理论上来就,一个人不犯罪完全是可能的。例如一个婴儿,在受洗之前就死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是没有罪的,可以进入天国。第三,既然罪是由我们自己所犯,那么弃恶从善也只能靠我们自己,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善功来解除罪孽。
可以说,一切宗教最后的心理原因,都是为了超越这种苦恼,都是为了给死亡问题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在基督教中,死亡是与原罪联系在一起的,用《圣经》里的话来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可见死是对罪的一种惩罚。所以亚当犯原罪的最恶劣的后果,就在于它使死亡从此成为我们人类的一种宿命。死既然是因为罪而来,那么罪的解除则意味着死亡本身的终结。所以基督耶稣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他以自己作为例证,向我们昭示了罪得赦免从而死而复活的希望(所以基督的死而复活被《圣经》比喻为灵魂得救的“初熟之果”)。这就是基督教神学中最具有精神感召力的救赎理论,它的意义就在于为信徒们解除了生存论危机,使他们在精神上超越了死亡。
他在《上帝之城》等一系列著作中,对佩拉纠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抨击,创立了维护原罪与救赎思想的预定论。针对佩拉纠的几个主要观点,奥古斯丁一一进行了驳斥。第一,亚当、夏娃的罪虽然是由他们自己犯的,但是他们一次滥用自由意志的结果,就造成了全人类万劫不复的原罪。亚当并非只是为我们做了一个坏榜样,而是从根本上败坏了人类的本性。通过某种遗传作用,亚当的原罪在他的子孙身上永远地延续下去。罪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本性之中,因此人性从根本上是邪恶的。第二,即使从理论上来说,世界上也没有一个人是无罪的,即使是呱呱坠地的婴儿,也同样为罪所控制。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描写了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当这个婴儿看到自己的母亲哺乳别的孩子时,他的眼里明显地流露出妒忌和愤怒的情绪。奥古斯丁因此得出结论,即使是刚刚出生的婴儿,仍然是有罪的。第三,由于原罪不是我们所犯的,因此我们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善功来解除原罪,我们充其量只能解除我们自己所犯的本罪,但是却无法解除亚当所犯的原罪。原罪的救赎只有靠上帝白白给予的恩典,靠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所以基督对于我们最终的罪得赦免和死而复活,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决定论的道德观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圣徒意识,在基督教的历史上,像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都具有这种强烈的圣徒意识。他们坚定不移地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并非出于个人的意愿,而是出于上帝的预定;不是他们自己要这样做的,而是上帝使他们非这样做不可。这种决定论的宗教信念和道德观,使得一个人在面对危难境况时,往往表现得比信奉自由意志的人更加坚定、更加勇敢、更加百折不挠和视死如归,因为他把自己的行为归结为一种神圣理由的必然结果。这就是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思想,它与佩拉纠的自由意志论是直接对立的。这种预定论思想表现了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它显然把拣选、预定、救赎与恩典,都归结为无法洞悉的奥秘了。
这种自由意志的“善功得救”理论,与奥古斯丁的预定论救赎观是背道而驰的,它造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社会的信仰虚假和道德堕落,最终激起了马丁·路德的义愤,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
经院哲学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第二大部分,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是接着教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或神学思潮的总称,它发展和盛行的时间大体上从公元11世纪一直到中世纪结束和近代早期。
经院哲学也是一种基督教哲学,在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笼罩一切的文化大背景下,它与教父哲学一样也是神学的奴婢。但是与教父哲学相比,经院哲学的理论根基已经不再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而是亚里士多德主义。我们在前面讲到亚里士多德主义不同于柏拉图主义的地方时,曾经强调亚里士多德主义是以理性和逻辑见长的。大家知道,教父哲学的理论基础是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它的基本特点是用信仰来排斥理性,即使是比较温和的观点,如奥古斯丁的观点,仍然也是坚持超理性的信仰或者“先信仰后理解”的立场。但是相比而言,经院哲学却表现出了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强调理性论证对于信仰的重要性。
关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在经院哲学内部也存在着各种意见分歧,比较温和的观点主张“信仰寻求理解”(如安瑟尔谟和托马斯·阿奎那),极力为基督教的各种教义提供理性的论证,这种观点构成了经院哲学的正统和主流;比较激进的观点则主张“理解导致信仰”(如阿伯拉尔),将理性当作信仰的前提,这种观点后来被罗马教会斥为异端。然而,无论是“信仰寻求理解”,还是“理解导致信仰”,这两种表面上对立的观点实际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强调理性对于信仰的重要性,这个基本特点与教父哲学的那种反理性的盲信立场是迥然而异的,
经院哲学对理性的重视,主要表现在它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所进行的理性论证,特别是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这些证明在逻辑上都存在着一些漏洞,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并不具有真正的说服力,但是它们的意义并不在于逻辑上是否完善,而在于它们表现了一种思想倾向,那就是试图用理性来证明信仰,这一点是与德尔图良等教父派的态度完全不同的。
生活在11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人安瑟尔谟(Anselmus,约1033—1109)通常被看作经院哲学的开创者,这位后来被罗马教皇任命为英国最高教职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神学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安瑟尔谟认为,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信仰而不去寻求理解,这乃是一种懒惰的表现,而懒惰无疑是一种罪过。与这种懒惰的态度相反,安瑟尔谟主张,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在有了信仰之后,进一步去寻求理解。他强调,我们固然不是因为理解了才去信仰,而是因为信仰了才去理解,这是不可动摇的前提,但是如果只是信仰而不去理解,这种态度同样也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如果我们在信仰之后能够进一步获得理解,那岂不是锦上添花吗?因此,安瑟尔谟就试图对基督教的一些基本教义进行理性证明,其中最经典的就是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
这个证明的大体意思如下:即使是一个愚顽人,他心中也会有一个最完美的东西的观点,而这个最完美的东西当然就应该是无所不包的(否则它就不是最完美的,而是有缺限的了),因此它也应该包含存在。上帝无疑就是这个最完美的东西,所以上帝存在。
大前提——最完美的东西应该包含存在(否则它就不是最完美的了)。
小前提——上帝是一个最完美的东西(因为“上帝”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绝对、无限和永恒)。
结论——所以,上帝存在。
安瑟尔谟的这种反驳,看起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的道理却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如果你相信“上帝是最完美的东西”,那么你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这个前提推出“上帝存在”这个结论。但是,如果你根本就不信仰上帝,不同意上帝就是最完美的东西,那么这个证明就变得无效了。
说到底,安瑟尔谟不过是在信仰之中兜圈子,他的本体论证明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但却仍然是以信仰作为绝对前提的。
康德就明确地指出,存在不同于美丽、善良、智慧等性质,它并不是事物的一种属性,而只是事物的一种状态。因此,一个事物是否存在并不会影响到它的完美性,而只是涉及这个事物的现实状态,即它是想象的还是实存的。
康德坚持认为,存在作为事物的一种状态,只能通过经验才能确定,它是决不可能仅仅从事物的概念中直接分析出来的。康德对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可谓是一针见血,所以自康德之后,很少再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上帝的存在了。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5—1274)是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哲学的重要代表,他与5世纪的奥古斯丁构成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两大理论支柱。
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一共有五个,包括四个宇宙论证明和一个目的论证明,这些证明通常被叫作“圣托马斯五路证明”。
阿奎那的几个宇宙论证明是这样的。
第一个证明是从经验的受动—推动系列推出一个世界的第一推动者。
任何一个经验事物都是被别的事物所推动,而推动者又进一步被第三个事物所推动,以此类推,我们必须终结于某个终极的推动者,否则就将陷入无限上溯的恶循环中。因此,我们必须断定这个受动—推动系列最后终止于某一点,它推动万物但是自身却不被其他事物所推动,这个终极的动力就是那“不动的推动者”或第一推动者,而它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
第二个证明是从经验的因果系列推出一个自因的“第一因”,这个“第一因”就是上帝。第三个证明是从偶然—必然系列推出一个绝对必然的存在,这个绝对必然的存在就是上帝。第四个证明是关于一个完美性系列的推理,最后推出了一个最完美的存在,那就是上帝。这三个证明的逻辑推理过程都与第一个证明一样,即从经验事实中追溯出一个终极的根据。
第五个证明是目的论证明,它是从人造物都具有目的性出发,推论出自然物也充满了目的性,从而论证一个作为造物主的上帝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件人造物都具有某种目的性,例如我们制造钟表是为了计时,制造杯子是为了喝水。但是在自然物中似乎也存在着某种目的性,也充满了一种智慧的痕迹,例如自然界有猫就有老鼠,猫存在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吃老鼠,而老鼠存在的目的好像就是为了被猫吃。这样一来,自然物的目的性就使我们很容易推论出一个目的的赋予者,那就是创造世界万物并赋予它们以特定目的性的上帝。以上就是著名的“圣托马斯五路证明”。
在他的那些证明中,同样也存在着两个很明显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诚如罗素所指出的,阿奎那的四个宇宙论证明都是建立在同一个理论假设之上的,这个理论假设就是:“没有首项的数列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阿奎那的四个宇宙论证明中,都先验地假定了一个终极的根据,在阿奎那看来,无论是受动—推动系列、因果系列还是偶然—必然系列、完美性系列,都必须追溯出一个首项(第一推动者、第一因、绝对必然的存在、最完美的存在等),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为什么这个世界必须要有一个首项呢?为什么没有首项的数列就是不可能的呢?罗素举例反驳了阿奎那的这种假设,他指出,以负1为末项的负整数系列就是没有首项的。
阿奎那证明的第二个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接受了“没有首项的数列是不可能的”这个理论假设,我们又是根据什么把基督教的上帝等同于这个首项呢?这个首项为什么不能是伊斯兰教的真主,或者唯物主义的物质呢?答案很清楚,仍然是由于信仰!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托马斯·阿奎那的那些证明在实质上与安瑟尔谟的证明一样,都是建立在信仰之上的。它们所具有的思想意义也与本体论证明一样,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成功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在于它们坚持用理性和逻辑来证明基督教信仰这样一种努力。
事实上,当经院哲学家们开始用理性来证明那些过去纯粹是诉诸于信仰的教义时,他们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把信仰架空了。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从单纯信仰到逻辑论证是第一步转变,从逻辑论证到感性直观则是第二步转变。
一旦人们开始对信仰的内容进行感性直观,开始追问信仰内容的具体细节,那么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整个基督教神学大厦也就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因为,当我们试图通过感性直观的方式来追问基督教教义的细节时,一切荒诞不经的结论就会应运而生。
因此,当经院哲学家们为信仰的内容寻求理解,然后再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进行感性直观时,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意识地损毁了基督教信仰的墙脚。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用感性直观的方式来对待晦涩教义的做法,恰恰开启了一个好的方向,那就是经验的方向。大家都知道,近代的思想,无论是科学思想还是哲学思想,都特别强调经验,都是以经验作为出发点的。因此感性直观虽然不利于基督教神学,但是却极大地有利于近代科学和哲学从中世纪的信仰氛围中脱颖而出。
因此我们说,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既不是一种客观意义的自然哲学,也不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知识论,而是一种关系到人的生命意义的生存哲学。只是在中世纪,这种生存哲学只能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真正的主角是人的主观精神,但是这种主观精神却不得不戴上了一副神的面具。因此在中世纪西欧社会,一切哲学问题最终都归结为神学问题。
在中世纪早期,即罗马帝国刚刚灭亡的“黑暗时代”,出现了一位名叫波爱修(Boethius,约477—524)的教父哲学家。波爱修对波菲利提出的共相问题进行了重新诠释,明确地把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确立为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的分界点。至于他本人,他是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上的。首先他认为,共相不是一个独立实在的东西,它只能是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此外他又认为,共相是无形的,只能寓于可感事物之中,并没有独立性。事实上,到了波爱修这里,他已经把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分歧简化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共相(或者种属、理念)到底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还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的普遍本质。
认为共相是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这无疑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而主张共相只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的一种抽象本质,这就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了。抽象的本质和客观的实体是不同的东西,客观实体是不依赖其他东西而独立存在的,而抽象的本质只是一种思想活动的结果,它只能存在于头脑之中。因此,这二者之间的差异,说到底就在于我们到底承不承认有一个脱离于个别的、具体的可感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理念或种属概念。与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分歧一样,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们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样也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条路线。在经院哲学中,凡是认为共相(理念、种属)可以独立于并且在逻辑上和时间上优先于具体个别的可感事物而存在,而且可感事物只不过是对共相的一种摹仿和分有的,这一类观点代表了柏拉图主义的(理念)实在论观点,因此被叫作实在论;相反,凡是认为共相并非独立于、而只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并且在逻辑上和时间上都要后于可感事物的,就被叫作唯名论,即认为所谓共相不过是一个主观的名称而已。
实在论有极端派和温和派,唯名论也有极端派和温和派。两个极端派当然是直接对立的,但是两个温和派的观点却比较接近。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在这里只能大致介绍一下这四个派别的基本观点。
极端实在论的代表就是那位提出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安瑟尔谟,他坚持认为共相是先于和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认为共相或概念比具体事物更加具有本质性。
尤其是安瑟尔谟在反驳高尼罗时明确表示,上帝的本质就已经先验地包含了存在,从上帝的概念中就可以绝对必然地分析出存在。这恰恰表明了实在论的基本观点,即本质先于存在,本质(共相、概念)分析地包含着存在(现象、具体事物)。
与极端实在论相对立的观点是极端唯名论,它的代表是与安瑟尔谟同时代的洛色林(Roscellinus,约1050—约1125)。洛色林曾经在英国与安瑟尔谟发生过公开的论战,与安瑟尔谟把共相实体化的做法针锋相对,洛色林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共相根本就不具有任何实在性,它不过是一个名词、一个声音,甚至就是一阵风或者空气的震动而已——因为声音是通过风或空气来传播的。
温和唯名论最重要的代表是阿伯拉尔(Abelard,约1079—1142)。
在关于共相的问题上,阿伯拉尔既反对实在论把共相实体化的观点,坚持认为真正实在的东西只是一个个的个别事物;同时他也指出,共相并不是像他的老师洛色林所说的那样,仅仅只是一个空洞的名词或者声音。阿伯拉尔认为,共相是一种概念,而概念本身是有其客观对象的,尽管这个客观对象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实体,但它却是寓于可感事物之中的一种普遍本质。
阿伯拉尔的思想非常接近于我们今天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一方面否认在个别事物之外独立存在的一般事物,另一方面又承认一般之所以为一般,就是因为它在每一个个别事物之中都有着某种客观的普遍本质。也就是说,我们虽然不同意普遍本质的独立实在性,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普遍本质就完全不具有客观性,仅仅是主观杜撰的结果。我们仍然承认在独立存在的个别事物之中具有某种客观的普遍本质,只不过这种普遍本质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通过思想的抽象活动才能把握,而这种思想的抽象活动就是形成概念的过程。所以我们认为,作为思想抽象活动结果的概念就是对事物的客观本质的一种主观反映,它所指称的就是事物的普遍本质,而不是个别现象。就这一点来说,阿伯拉尔的观点可以被称为“概念论”。概念论既反对把共相说成是独立实体的实在论,同时又超越了把共相仅仅归结为一种主观名称的极端唯名论,它认为共相固然不是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但是它在个别事物中又有其客观性的根据。这种观点就比较折中了,因此是一种温和的唯名论观点。
温和实在论的著名代表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托马斯·阿奎那,他以一种辩证的观点来解释共相与个别事物之间的关系,显示出较高的理论水平。阿奎那认为,共相既是先于、又是寓于、而且是后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
阿奎那用一种神学的观点来说明二者的关系:第一,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万物的共相就已经以一种理念的形式存在于上帝的头脑中。
第二,阿奎那又认为,当世界被创造出来以后,共相就不再是作为一个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东西了,它只能寓于个别事物之中,不可能再与个别事物相分离。
第三,阿奎那指出,当我们认识事物的时候,我们是首先认识感性的个别事物,然后再通过抽象的思维,从感性的个别事物中抽出它的一般本质或共相。所以,共相作为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在认识过程中又是后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阿奎那的这种认为共相先于、寓于和后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观点,表达了一种在直接对立的实在论和唯名论之间寻求妥协的折中态度,它实际上已经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把唯名论的观点纳入到实在论之中。因此,我们把托马斯·阿奎那关于共相的观点称为温和实在论。
在阿伯拉尔和托马斯·阿奎那之后,经院哲学内部又出现了几位晚期唯名论者,他们就是著名的方济各修会“三杰”——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9—约1292)、邓斯·司各特(Duns Scotus,约1265—1308)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1285—1347)。这三位杰出的经院哲学家在思想上都是反托马斯·阿奎那的,他们与阿奎那也不在同一个修道会。
方济各修会的“三杰”罗吉尔·培根、邓斯·司各特和奥卡姆的威廉都是英国人,关于他们三个人的观点,我们从总的方面来概括一下。
第一,他们都特别强调经验的重要性,主张从经验出发来认识世界。
第二,他们在神学上基本上都是一些神秘主义者,认为上帝最重要的特点不是理性,而是意志。上帝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做出在我们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上帝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人类通过自己的理性是无论如何也认识不了上帝的,经院哲学家们关于上帝存在和本性的一切逻辑论证都是无效的。特别是司各特和奥卡姆,他们通常被称为唯意志主义者,这种唯意志主义当然就与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反对用理性来认识上帝和把握神学教义,认为基督教的教义都是极高的奥秘,人是无法认识的。这种观点似乎有点像是回到了早期教父派的观点。而他们之所以主张这种观点,并不是由于愚昧,而是由于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用理性来证明上帝存在的做法。
第三,这三位方济各修会的思想家在共相问题上都属于唯名论者,他们都认为在个别事物之外并不存在独立实在的共相,共相只不过是对个别事物共性的一种主观反映而已。他们否认共相先于个别事物的观点,却坚持共相寓于个别事物(从存在论角度)和后于个别事物(从认识论角度)的观点,因此他们的观点是与托马斯·阿奎那的温和实在论相对立的。
这些英国经院哲学家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坚持把神学与哲学分离开来,反对用哲学来论证神学。他们主张信仰归信仰,理性归理性;神学归神学,哲学归哲学。在神学方面他们基本上都是神秘主义者,但是在哲学方面他们却是经验主义者。
![图片[1]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哲学】《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个人摘录(第七讲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小竹の笔记本](https://img.smallbamboo.cn/i/2025/09/18/68cba8e7b2b8d.jpg)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662629/
说明:本文每一行均为部分摘录,阅读连贯性可能较差,个人存档用,推荐购买正版书籍阅读。
2. 论文总结类文章中涉及的图表、数据等素材,版权归原出版商及论文作者所有,仅为学术交流目的引用;若相关权利人认为存在侵权,请联系本网站删除,联系方式:i@smallbamboo.cn。
3. 违反上述声明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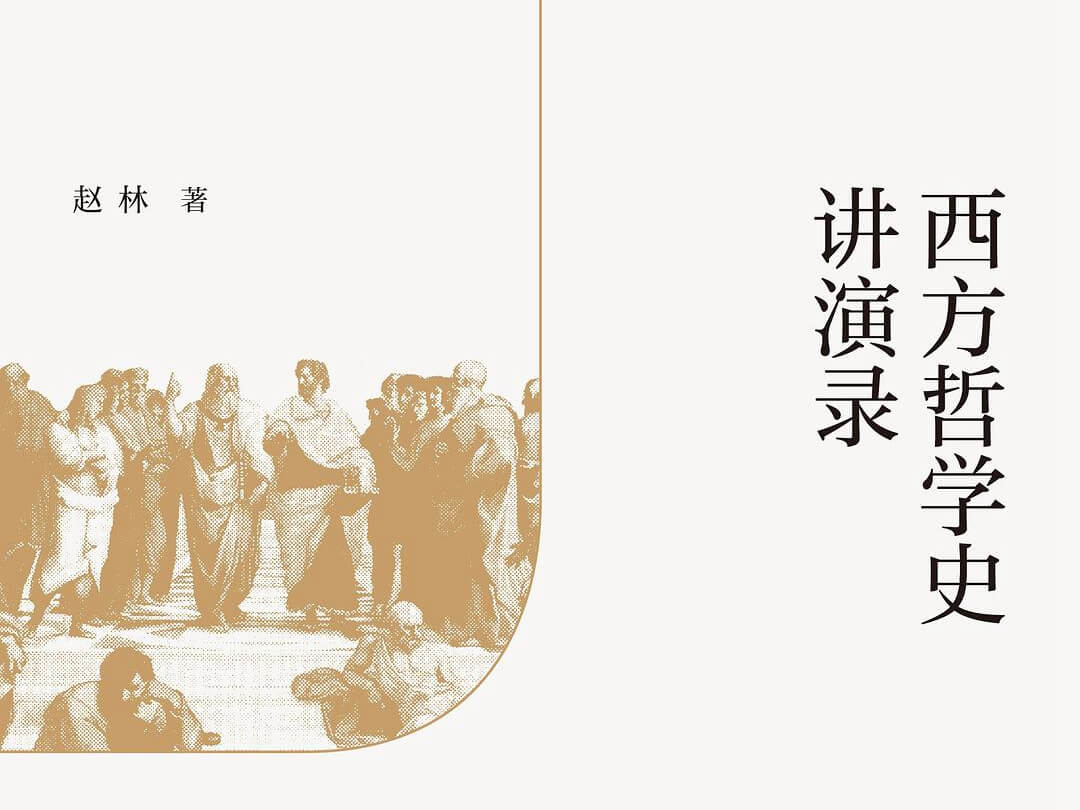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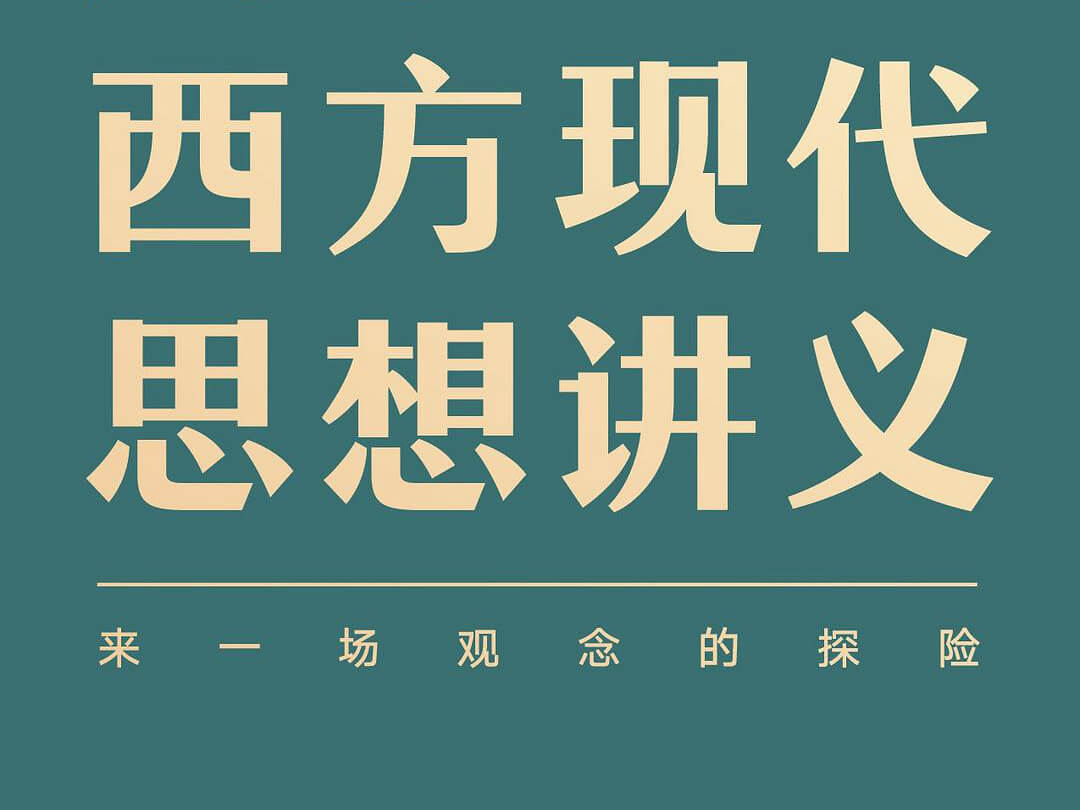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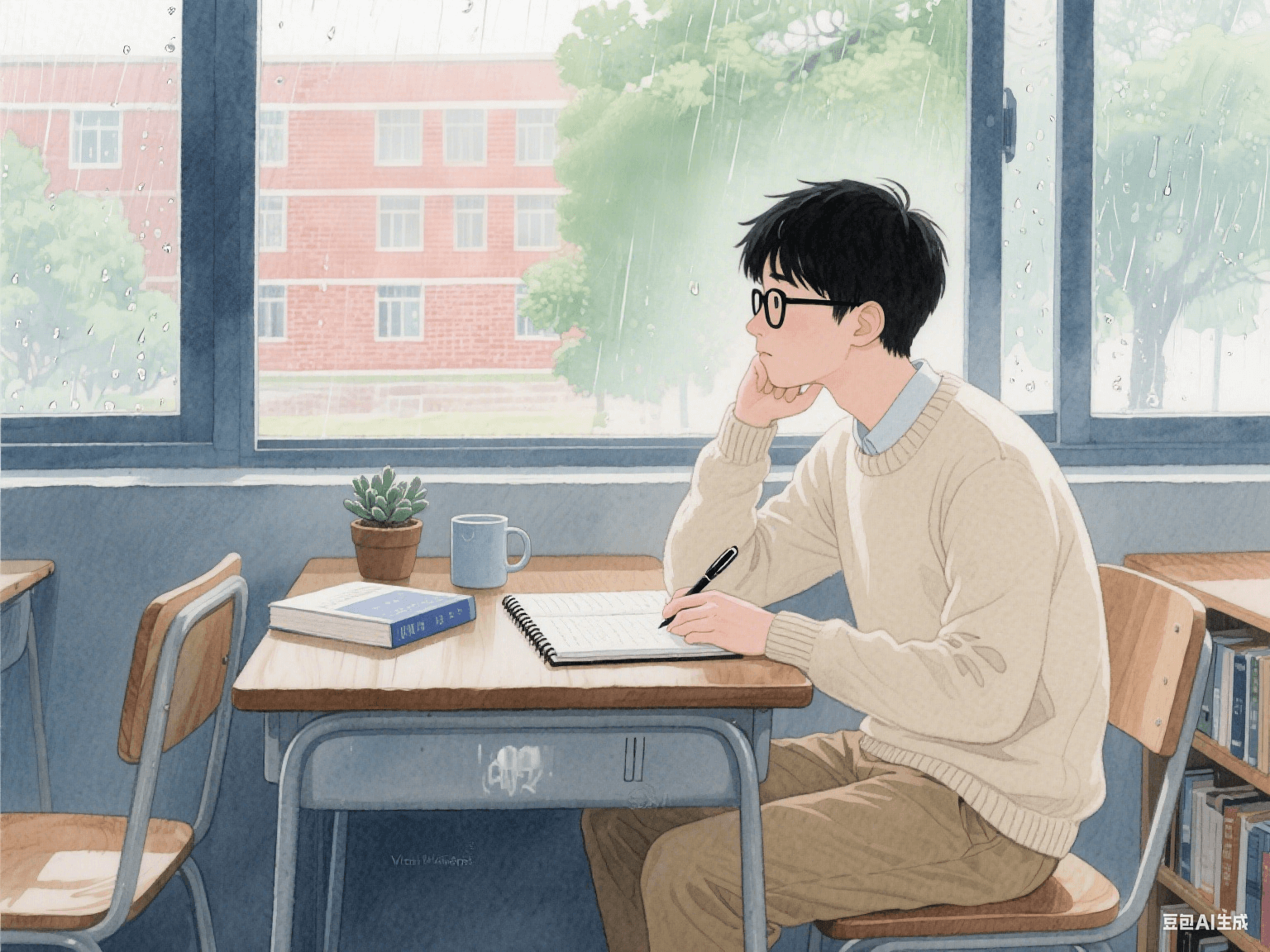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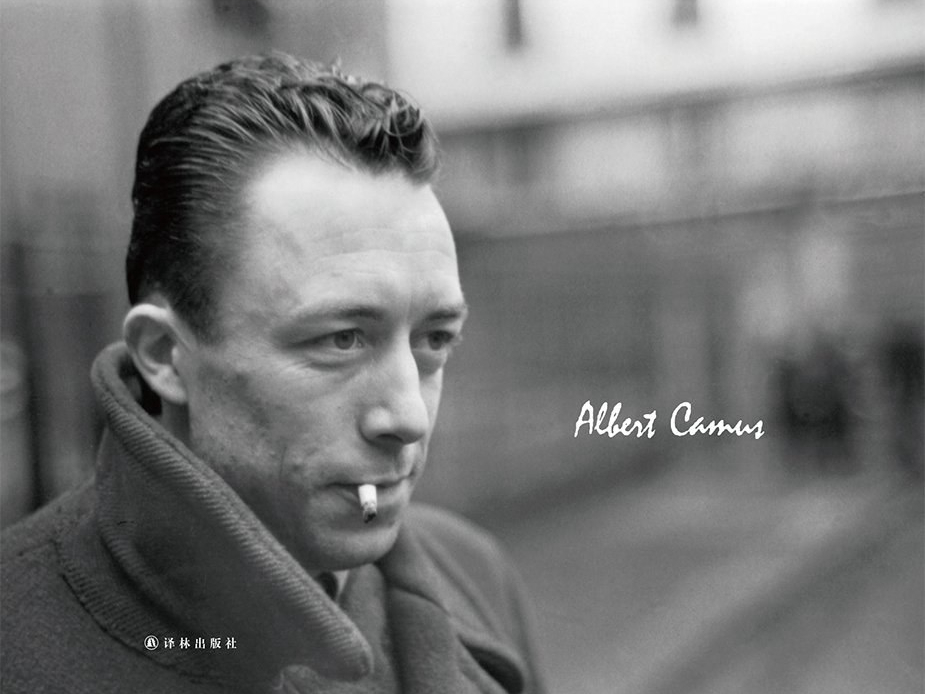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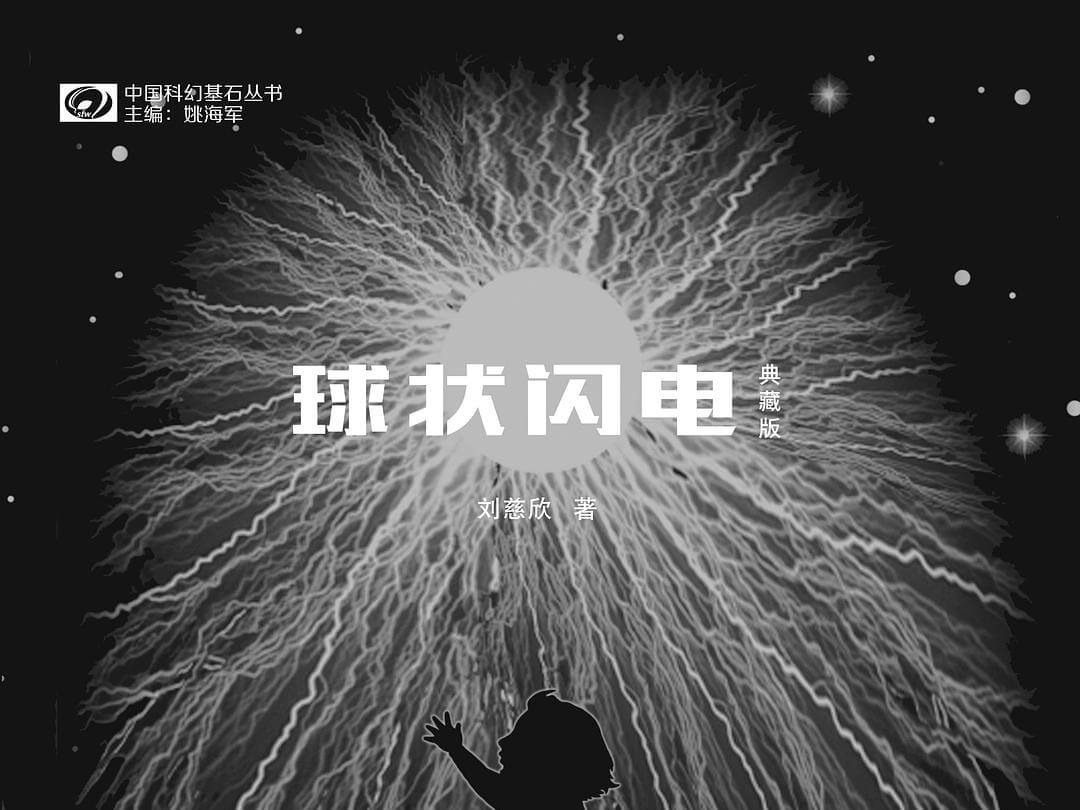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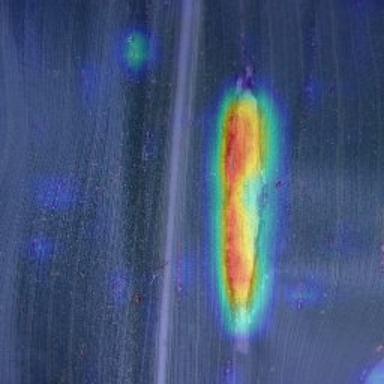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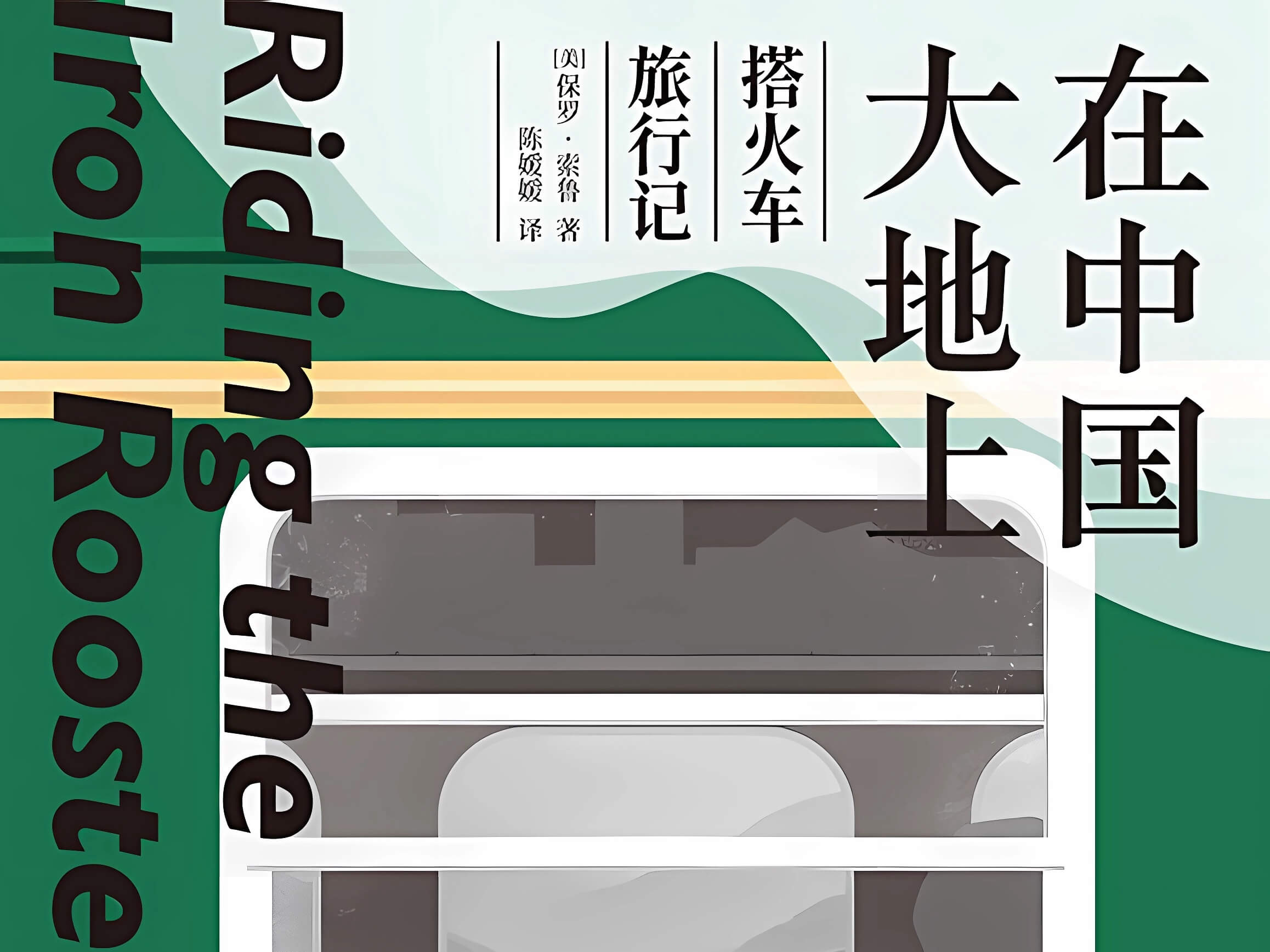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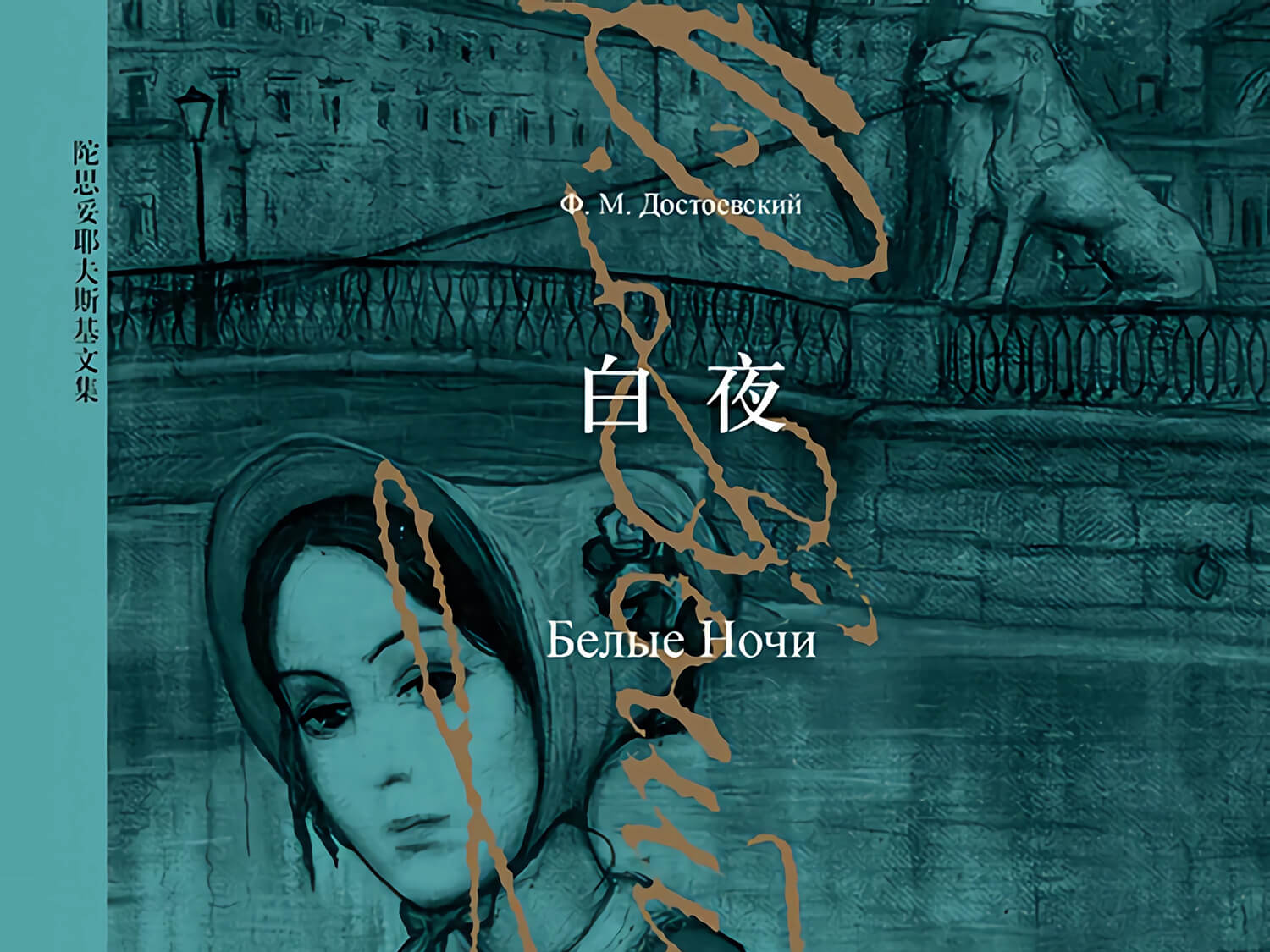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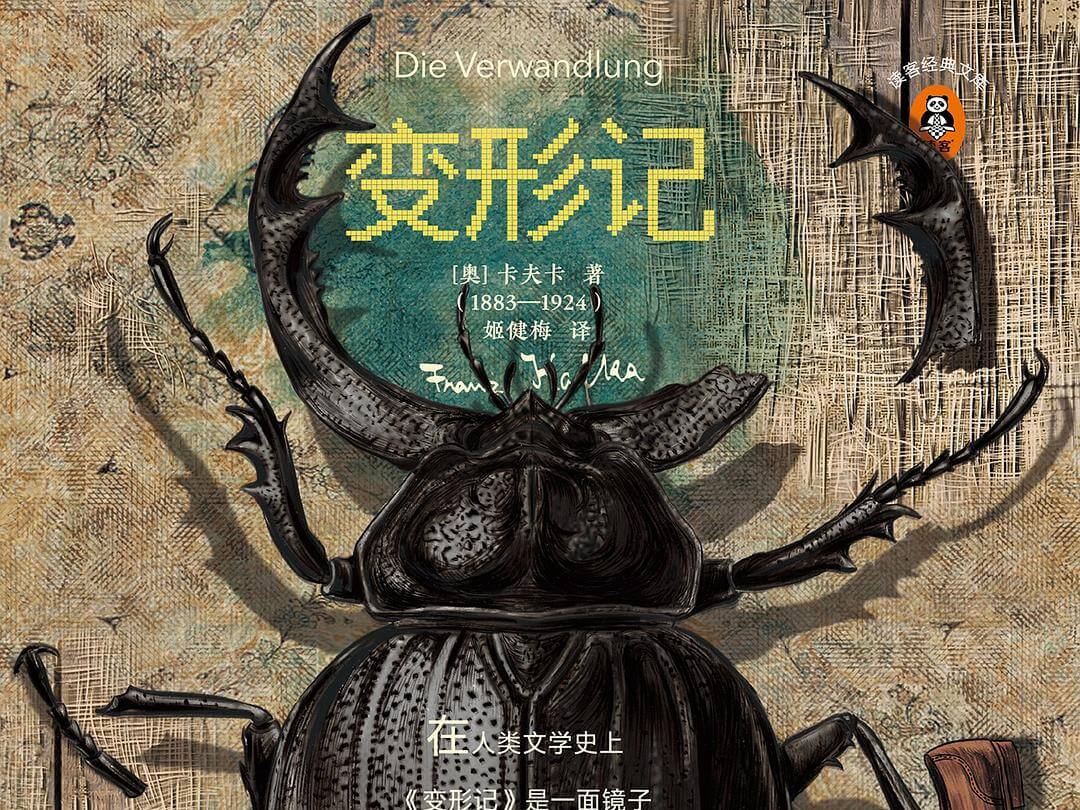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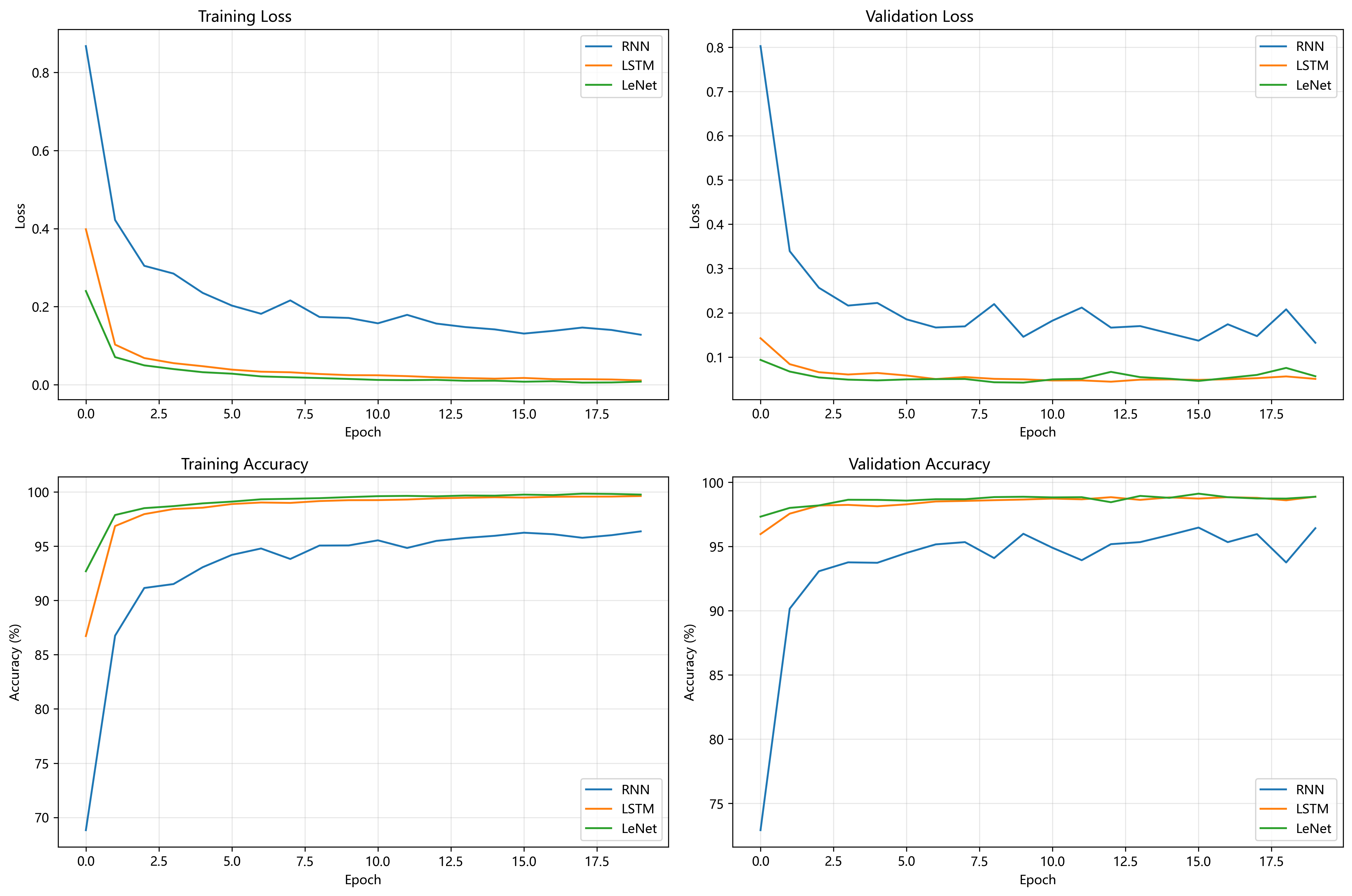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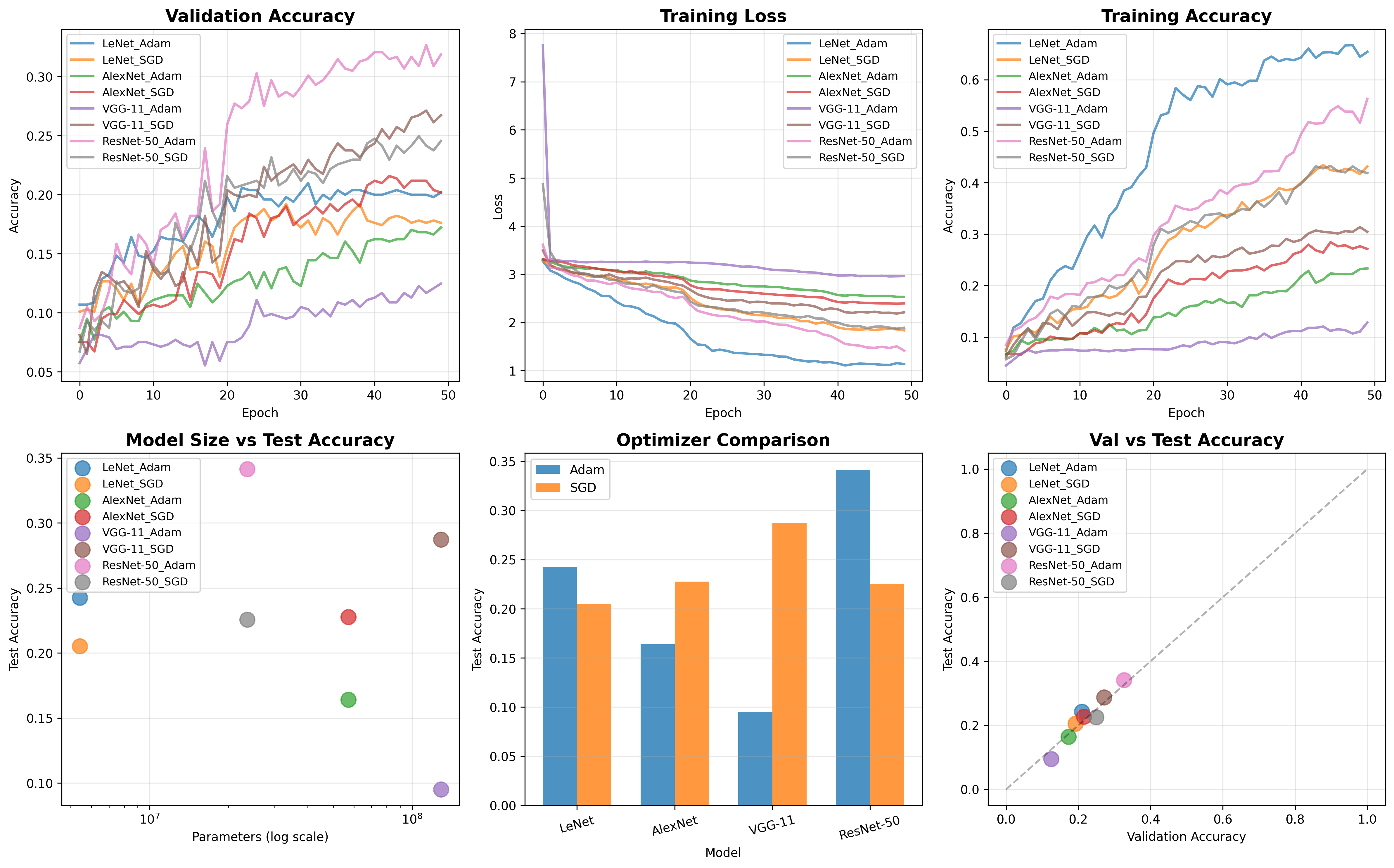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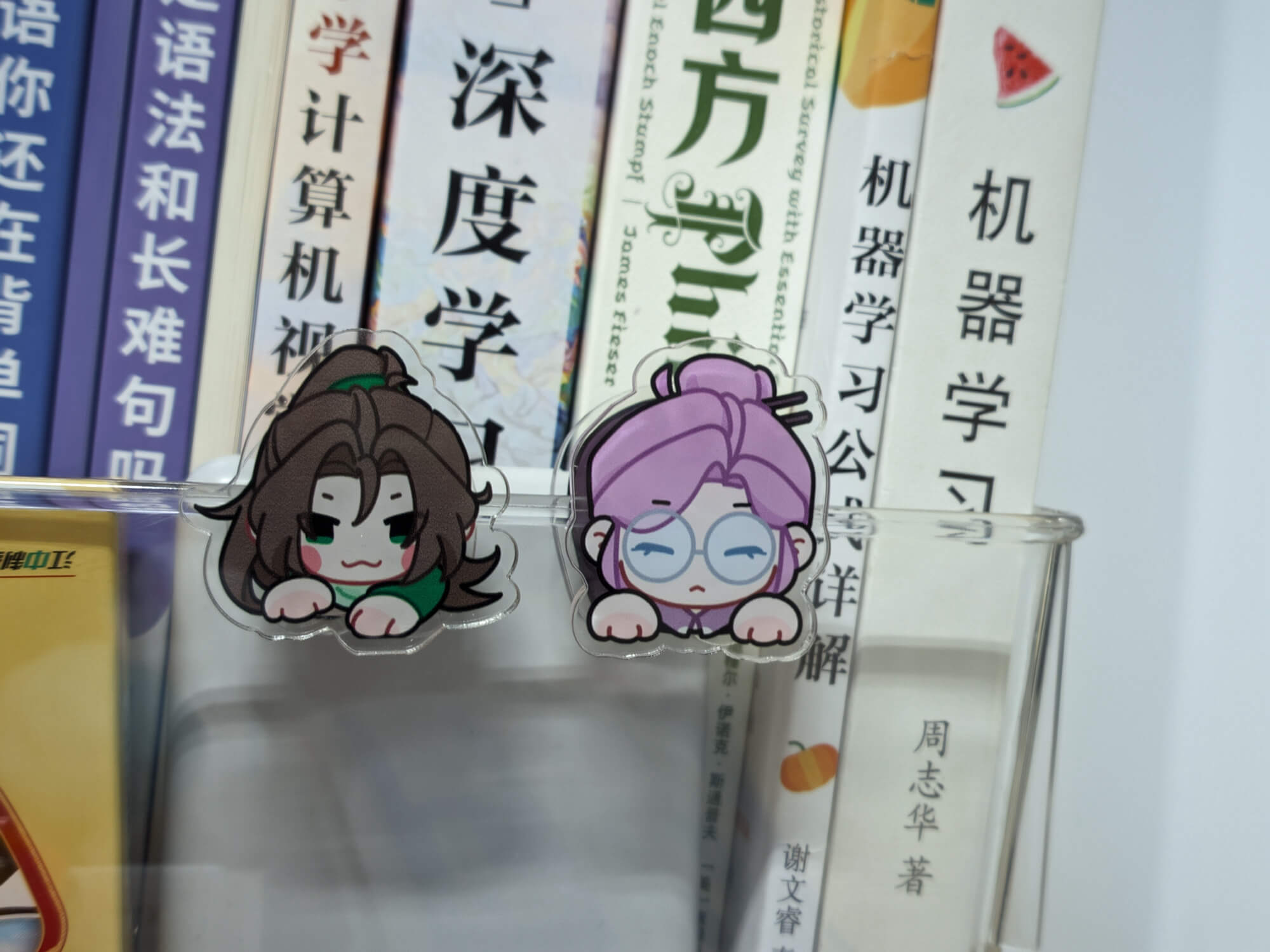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