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包含了加缪的三篇小说:《局外人》,《鼠疫》和《堕落》。本文是其中《鼠疫》的摘抄与总结。
——达尼埃尔·笛福
第一部
阿赫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因此,没有必要确切介绍我们这儿的人们如何相爱。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中飞快地互相满足,要么双双安于长期的夫妻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折中。这也并不独特,在阿赫兰跟在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
在他经过的一条街上,他数了数,有十二只死老鼠扔在残羹剩菜和脏布碎片当中。
市府却从未有过什么准备,也不曾考虑任何措施,只召集了首次会议进行讨论。灭鼠处奉命每日凌晨收集死老鼠。收集完毕,处里派两辆汽车将死动物运往垃圾焚化厂焚烧。
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里厄大夫刚把汽车停在他居住的大楼门前,就瞥见老门房正从大街的尽头走过来,他走路非常吃力,歪着脑袋,双臂和双腿叉开,活像牵线木偶。
可以说,门房的死标志着一个令人困惑的迹象丛生的时期已经结束,另一个更为艰难的时期业已开始,在这之后一个时期,起初的惊异正在逐渐变成恐慌。我们的同胞先前从未想到我们这个小城会特别选定为老鼠死在阳光下、门房得怪病送命的地方,今日伊始,他们对此不再怀疑了。从这个观点看,他们过去总归是错了,他们的想法有待纠正。倘若一切到此为止,那么习惯成自然的势力无疑会占上风。然而,我们同胞中的其他一些人,他们既非门房,也非穷人,却接连走上了米歇尔先生带头走过的路。就从这一刻起,人们开始感到恐惧,同时也开始思考。
“我可没办法,”里沙尔说,“这事儿应该由省里采取措施。再说,谁告诉您这病有传染的危险?”“谁也没有告诉我,但这些症状令人担忧。”
报纸在老鼠事件里喋喋不休,对死人的事却只字不提。原因是老鼠死在大街上,而人却死在他们自己的房间里。报纸只管街上的事。不过省政府和市政府已在开始考虑问题了。但只要每个大夫掌握的病例不超过三两个,便没有人想到要行动。其实,如果有谁想到把那些数字加一加就好了,因为加起来的数字是触目惊心的。
舆论,很神圣嘛:它说不要惊慌,千万不要惊慌。还有,正如一位同行说的:‘这不可能,谁都知道,瘟疫已在西方绝迹了。’不错,谁都知道,除了死者。
他们不相信天灾。天灾怎能和人相比!因此大家想,这灾祸不是现实,它只是一场噩梦,很快就会过去。然而,噩梦不一定会消逝,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逝去的却是人,首先是那些人文主义者,因为那些人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他们自以为无拘无束,但只要大难临头,谁都不可能无拘无束。
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
有两三个医生叫了一声。其余的人似乎犹豫不决。至于省长,他惊得微微一颤,下意识地转身朝门那边看看,仿佛想核实房门是否真的阻止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消息传到走廊上。
沉默片刻,里厄说:“细菌能在三天之内引起脾肿大四倍,能使肠系膜淋巴结肿到橙子那么大,摸起来像浓稠的糊状物,这恰恰不容许我们再犹豫下去。各种传染源正在不断扩大。照疫病目前的传播速度,如果再不停止,就可能在两月之内夺去城里一半居民的生命。因此,叫它鼠疫或增长热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你们得阻止它夺去城里一半人的生命。”
里厄坚持说道:“问题不在于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厉,而在于是否有必要采取那些措施以阻止一半市民送命。其余的事属于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我们的体制恰巧规定要有一位省长来解决这些问题。”
医生磋商会的第二天,高烧病人又激增了些。连各家报纸都提到了,不过都是轻描淡写,仅仅暗示一番而已。
但后来疫情一下子又直线上升了。在日死亡人数重新达到三十来人那天,省长递给贝尔纳·里厄一份官方拍来的急电,里厄边看边说:“他们害怕了。”电报上写着:“宣布进入鼠疫状态。关闭城市。”
第二部
然而无须多久,受困于鼠疫的人们便明白过来,他们那样做是在把亲人往火坑里推,便终于下定决心忍受离愁别痛。
因此,鼠疫带给同胞们的第一个感觉是流放感。
这一来,人人都必须安心望着老天混日子。时间一长,这种普遍的懒散有可能锤炼人的性格,但眼下已开始让人变得斤斤计较、琐琐碎碎了。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在起变化,那就是里厄本人。这天晚上,他站在共和国雕像之下感到了这点,他一直注视着朗贝尔走进去的那家旅馆的大门,意识到一种让人别扭的冷漠已开始主宰了他。
令人精疲力竭的几个星期过去了,暮色中,全城的人照样拥到街头遛弯儿,在经历了这些日子之后,里厄这才悟出,他再也不必费力压抑自己的怜悯心了,因为在怜悯已起不了作用时,人们对怜悯会感到厌倦。在这些负担沉重的日子里,大夫找到了唯一使他宽慰的东西,那就是慢慢闭锁情感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真正的原因是,一方面,关闭城市、封锁港口使海水浴成为不可能;另方面,百姓处于一种极其特殊的思想状态:他们虽然在内心深处并没有接受这些事变的突然袭击,他们却明显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起变化。
上帝的光辉离我们而去,我们便长期陷在鼠疫的黑暗之中!
可以说,只要人不死,每过一天,人们就更接近这次苦难的终点。里厄不得不承认这观点的正确性,但这样概括事实未免太笼统。
城门边发生了斗殴,宪兵不得不动用武器,因此而引起了暗中的骚动。各家报纸都登载了政府的命令,政令一再重申禁止出城,并威胁违者将被逮捕下狱。
人们清楚地看到,春天大势已去,她曾在姹紫嫣红中出尽风头,如今却在暑热和瘟疫的双重压力下气息奄奄,缓缓逝去。
鼠疫肆虐中的酷日扑灭了一切色彩,赶走了一切欢乐。
但笔者更愿意相信,过分重视高尚行为,结果反而会变成对罪恶间接而有力的褒扬。因为那样做会让人猜想,高尚行为如此可贵,只因它寥若晨星,所以狠心和冷漠才是人类行为更经常的动力。而这种想法正是笔者不能苟同的。人世间的罪恶几乎总是由愚昧造成,人如果缺乏教育,好心也可能同恶意一样造成损害。
第三部
正是这些事故逼迫当局将宣布瘟疫状态和宣布戒严进行比较,从而实施相应的法律。
他们相当形象地代表着我们已经进入的僵化的独裁统治时期,起码代表这个统治时期最高的秩序,即一座大古墓的秩序,在这座大古墓里,鼠疫、石头和黑夜最终会窒息所有的声音。
再也没有时间去琢磨周围的人如何死去,他们自己某一天又如何死去。
在整个夏末那段时间,秋雨绵绵,每到深夜,都能看见一列列无乘客的奇怪的电车摇摇晃晃地行驶在沿海峭壁轨道上。居民们到最后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巡逻队禁止上峭壁道路,还是有一群一群的人经常溜到俯瞰大海的岩石之间,趁电车经过时将花抛进拖车里。那时,在夏夜里,总能听到满载鲜花和死人的车辆还在那里颠簸。
无论如何,正是这种现实的明白无误性,或曰对现实的感知使同胞们保持着流放感和别离感。
在鼠疫的第二阶段,他们连记忆力都失去了。并非因为他们忘记了亲人的面容,而是因为——这也一样——那已不再是有血有肉的面容,他们在体内已感觉不到亲人的存在。
总之,是那逐渐充满整个城市的无休无止、令人窒息的沉重脚步声,它夜复一夜,以最忠实最忧郁的音调呼应着那盲目的执著之情,这种情绪终于在我们心中取代了爱情。
第四部
里厄和他的朋友们这才发现他们疲惫到了什么程度。事实上,卫生防疫队的人员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疲劳了。里厄是在注意到朋友们和他自己身上正在滋长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时才发现这一点的。
今天,上帝施恩于他创造的人,将他们置于如此巨大的灾难之中,使他们重新寻找并实行这至高无上的德操:“全信”或“全不信”。
神甫又拒绝了,但进一步作了些老太太听来十分含糊的解释。她认为她只听懂了这一点(而她认为恰恰是这一点难以理解):神甫之所以拒绝看病,是因为看病不符合他的原则。她因此得出结论说,她的房客被高烧弄得头脑糊涂了,于是她仅仅给他提供了一些草药汤。
这种反讽意味的口号是某些游行示威的信号,尽管示威很快被制止了,它们的严重性却有目共睹。
自然,各家报纸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宣扬乐观主义。一读报纸,就会看见对当前形势特点的描写,那就是:居民表现为“沉着和冷静的动人典范”。然而,在一个自我封闭、无密可保的城市里,谁也不会欺骗自己去相信什么共同作出的“典范”。
为此,我决定拒绝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不论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论它有理无理。
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
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
从现在到那个时刻到来时,我深知我对这个世界本身已没有价值,从我放弃杀人那一刻起,我已经自我宣判永远流放。该由别的人来创造历史了。
我只不过想说,当今世界上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必须尽可能避免站在祸患一边。
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可以探索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即是说,怎样才能获得安宁。
塔鲁起身倾听,却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去防波堤。说到底,只在鼠疫圈子里生活实在太愚蠢了。当然,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但如果他除此就别无所爱,他斗争又有什么意思?”
响彻教堂的不是感恩的歌唱而是悲哀的呜咽。在这座死气沉沉、寒冷彻骨的城市里,还可以看到几个孩子在奔跑嬉戏,他们哪儿知道他们的生命正在受到威胁!
塔鲁望着窗外,好像是这个场景的局外人。
从一些人家的房梁上,又传出了好几个月没有听到的闹声。里厄等着每周伊始发表的全市统计总数,数字表明,鼠疫势头正在减弱。
第五部
从那一刻起,同胞们虽然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其实都很乐意谈论鼠疫结束之后如何重新安排生活的问题。
过去,医生采取的每项措施都毫无结果,如今,那些措施却似乎突然弹无虚发了。
疫病已放弃阵地,幸存者已稳操胜券。
然而,正当鼠疫似乎已启程回它悄悄出走的不为人知的老巢时,据塔鲁笔记的记载,城里至少有一个人为它的离去而惊慌失措,那就是柯塔尔。
塔鲁回到家里便记下了刚才那一幕,而且立即(有笔迹作充分证明)提到他很疲劳。他补充写道,他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不能以此作为理由让自己不作准备,他还问自己是否真正做好了思想准备。最后,他回答说,无论日间还是夜里,人总有一个时辰是怯懦的,他怕的正是这个时辰,他的笔记到此也就结束了。
“谢谢。我并不想死,我还要斗争。但如果仗已经打输了,我就愿意有一个好的终结。”里厄俯下身,紧紧按住塔鲁的肩膀,说道:“别这么说。要想成为圣人,就得活下去。斗争吧!”
最后,竟是他那无能为力的眼泪使他未能看见塔鲁猛然转过身去,面对墙壁,仿佛体内某处的主弦断了似的,低沉地哼了一声便与世长辞了。
接下来的夜晚已没有斗争,只有肃静。
里厄不知道塔鲁是否终于找到了安宁,但至少在此刻,他相信自己跟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或掩埋了朋友的成人一样,永远不可能再找回安宁了。
在二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各道城门终于在黎明时分打开了,这个举措受到本市居民、报纸、电台以及省府公报的欢呼致意。盛大的庆典活动不分昼夜。
不错,鼠疫连同恐怖都结束了,那些紧缠在一起的手臂说明,在深层意义上,鼠疫本来就意味着流放和分离。
是的,所有的人都曾在肉体和精神上一起经受过痛苦:难以忍受的空虚、无可挽回的分离、不能满足的欲求。
他们想去的地方正是他们的故乡,正是他们幸福之所在,而对其余的一切,他们都嗤之以鼻。
然而,至少有一个同胞,里厄大夫不能为他说话。那就是塔鲁有一天向里厄谈到的那个人,塔鲁说:“他唯一的真正罪行,就是从心底里赞成置儿童和成人于死地的那东西。其余的事我都能理解,但对这一点,我只能说不得不原谅他。”那人内心愚顽、孤独,此书以他为结束恰到好处。
那老头说得对,人永远是一个样。但不变的是他们的精力和他们的无辜,而正是在这里,里厄超越了一切痛苦,感到自己和他们心心相印了。
里厄大夫正是在这一刻下决心编写这个故事,故事到此为止,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
不过,里厄也明白,这本编年史不可能是一本最后胜利的编年史,它无非显示了人们在当时不得不做了些什么,并指出今后如遇播撒恐怖的瘟神凭借它乐此不疲的武器再度逞威,所有不能当圣贤、但也不容忍灾祸横行的人决心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努力当好医生时,又该做些什么。
在倾听城里传来的欢呼声时,里厄也在回想往事,他认定,这样的普天同乐始终在受到威胁,因为欢乐的人群一无所知的事,他却明镜在心:据医书所载,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能在家具、衣被中存活几十年;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有一天,鼠疫会再度唤醒它的鼠群,让它们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们再罹祸患,重新吸取教训。
总结
主题
①命运与人类困境
鼠疫作为一种突发的天灾,象征着人类生存中普遍存在的荒诞和无常。它突然降临,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迫使个体直面生命的脆弱、死亡的威胁以及与亲人的分离,揭示了人类在巨大天灾面前的无助。小说展现了人们从最初的否认、麻木,到逐渐认识并接受灾难的现实,反映了人类面对宿命的普遍心理历程。
②反抗与人道主义
面对荒诞的命运和无意义的苦难,小说中的主人公(特别是里厄医生和塔鲁)并没有选择屈服或逃避,而是积极投身于抵抗鼠疫的斗争。这种斗争不是为了彻底消灭鼠疫(因为加缪认为荒诞是永恒的),而是通过持续的、集体性的反抗来维护人类的尊严和价值。这体现了加缪的“反抗”哲学:尽管生活无意义,但人类可以通过行动、团结和对他人的关怀来创造意义,并展现人性的光辉。小说赞扬了那些在绝望中仍坚守岗位、无私奉献的普通人,他们的行动本身就是对荒诞的一种反抗。
③团结与个体责任
鼠疫的爆发打破了个人生活的界限,迫使所有人作为一个整体来面对共同的威胁。小说强调了在危难时刻,个体的责任和集体的团结对于战胜灾难的重要性。里厄医生、塔鲁以及卫生队的其他成员,他们并非英雄,只是普通人,但他们选择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共同对抗瘟疫,这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共同承担苦难的普世价值。
④恶与良知
鼠疫也象征着世间一切形式的“恶”和“不义”,包括战争、压迫以及人性中的冷漠和自私。小说探讨了人类如何面对并对抗这些恶。里厄医生拒绝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这代表了一种对良知和道德底线的坚守。而柯塔尔则代表了那些从灾难中获益或内心滋生邪恶的人,与里厄等人的反抗形成了对比。
⑤记忆与警示
尽管鼠疫最终退去,但小说结尾里厄医生清醒地认识到鼠疫杆菌“永远不会死绝,也不会消失”,它们“在房间、地窖、旅行箱、手帕和废纸里耐心等待”。这暗示了灾难和邪恶的循环往复性,也就是永恒的荒诞,以及人类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小说因此也具有一种警示意义,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要时刻准备好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挑战,并铭记那些在灾难中展现出的崇高人性。
荒诞与反抗
荒诞体现在小说中的多个方面。包括突如其来的无意义灾难、生命脆弱与死亡的随机性、人类经验的隔离与异化、官方的无能与欺骗等。而反抗则体现在:清醒的认识与不妥协的行动、坚持人道主义的团结与互助、对生命的热爱与超越个人苦难和诚实与拒绝谎言。
最后,加缪并非主张虚无和绝望,而是强调人类在明知荒诞的情况下,通过清醒的意识、积极的行动、相互的关怀和对道德底线的坚守,去勇敢地反抗这种荒诞,从而创造出属于人类的尊严和意义。这种反抗不是为了胜利,而是为了存在本身,为了证明人类即使在绝境中也能展现出超越动物性的伟大。
![图片[1]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阅读】《鼠疫 – 加缪全集:第一卷》摘抄&总结——《鼠疫》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小竹の笔记本](https://img.smallbamboo.cn/i/2025/06/13/684be31420e9f.jpg)
2. 论文总结类文章中涉及的图表、数据等素材,版权归原出版商及论文作者所有,仅为学术交流目的引用;若相关权利人认为存在侵权,请联系本网站删除,联系方式:i@smallbamboo.cn。
3. 违反上述声明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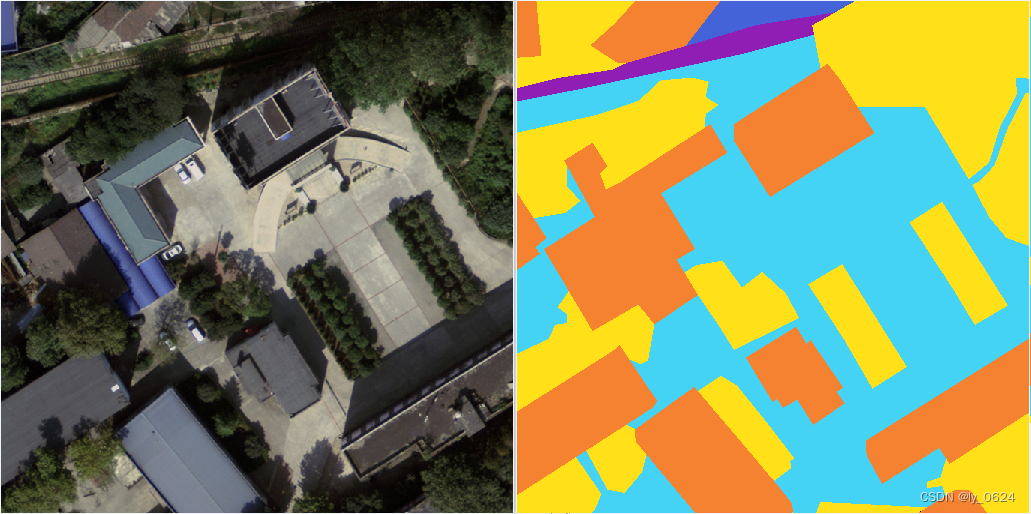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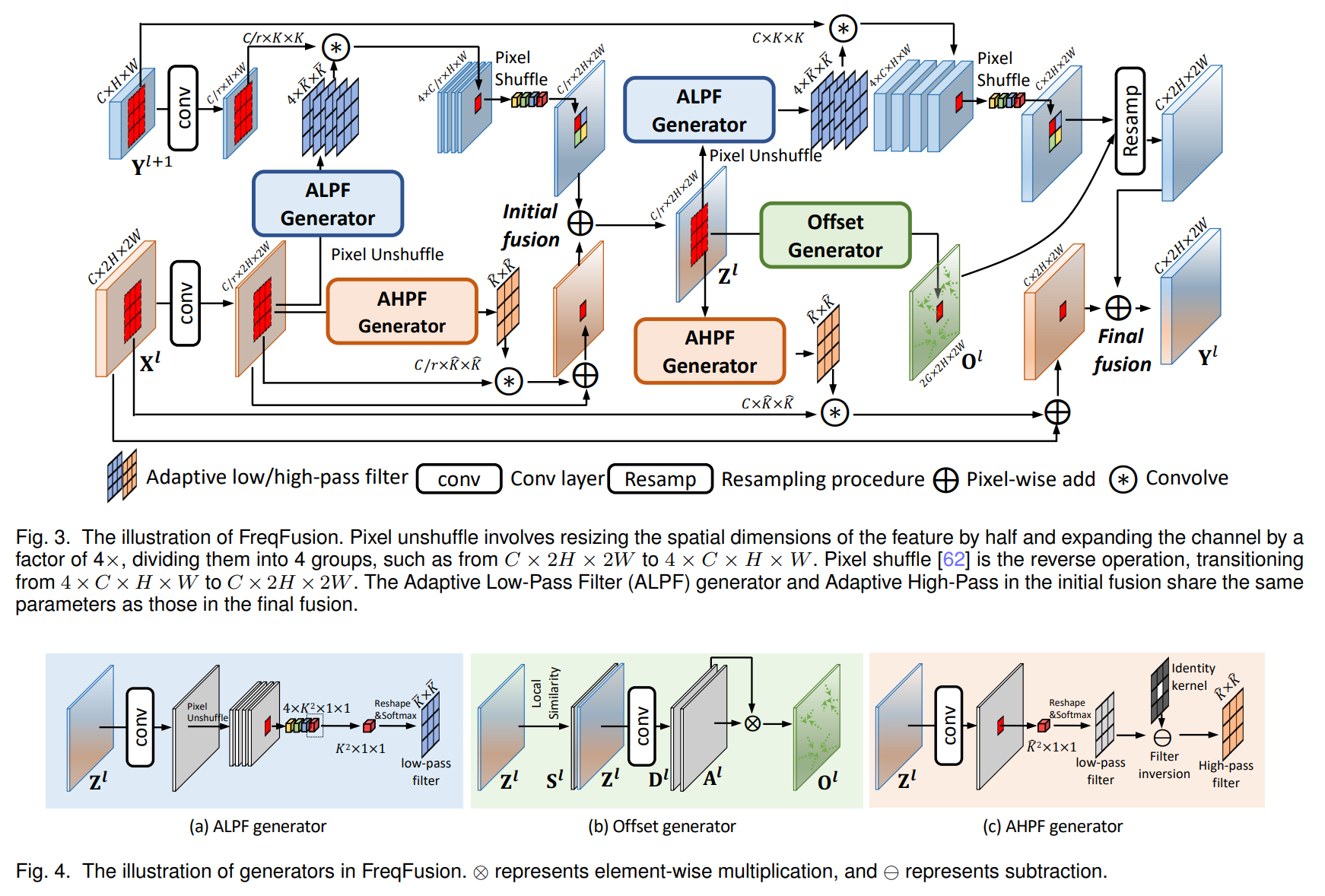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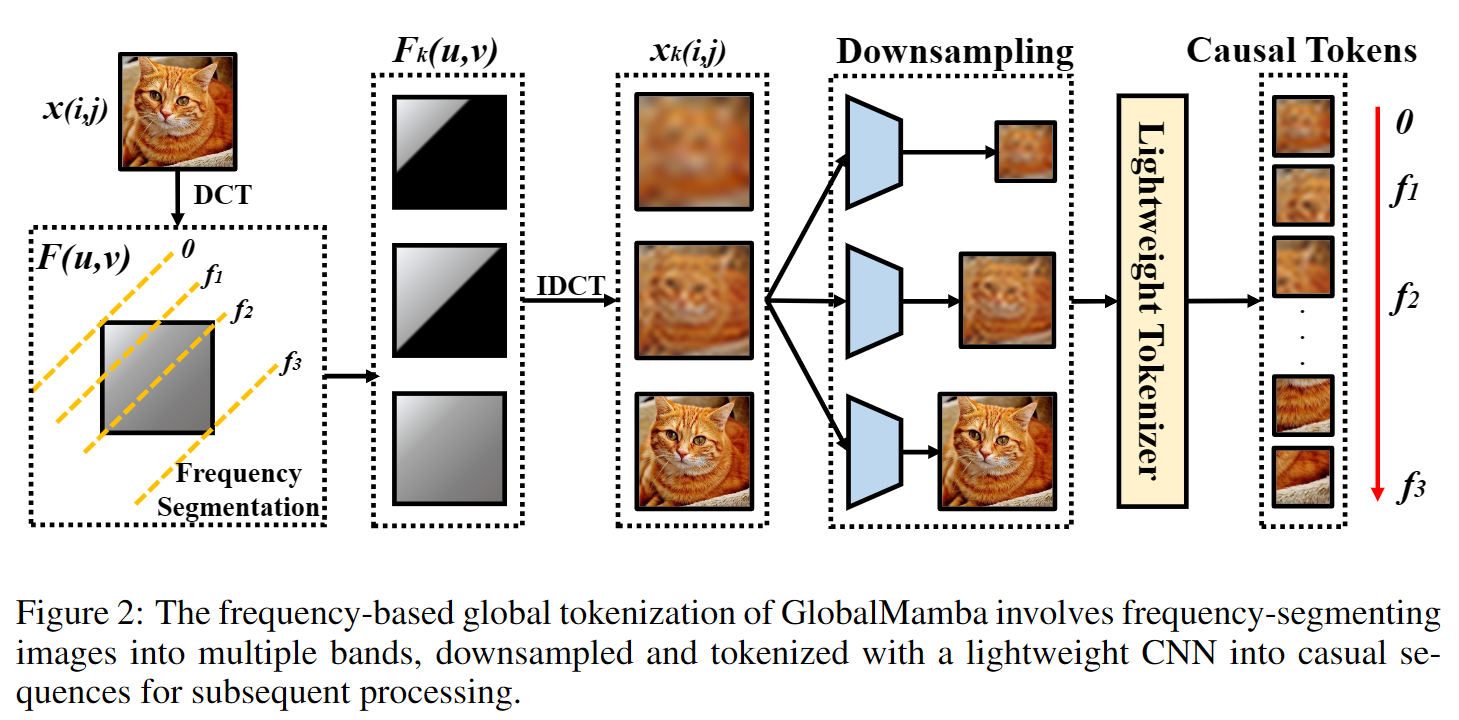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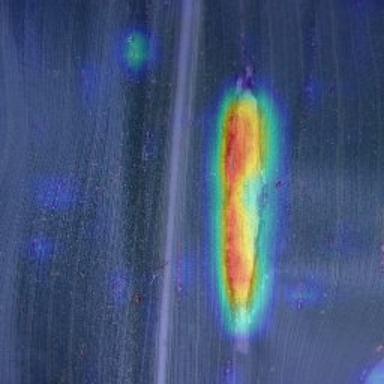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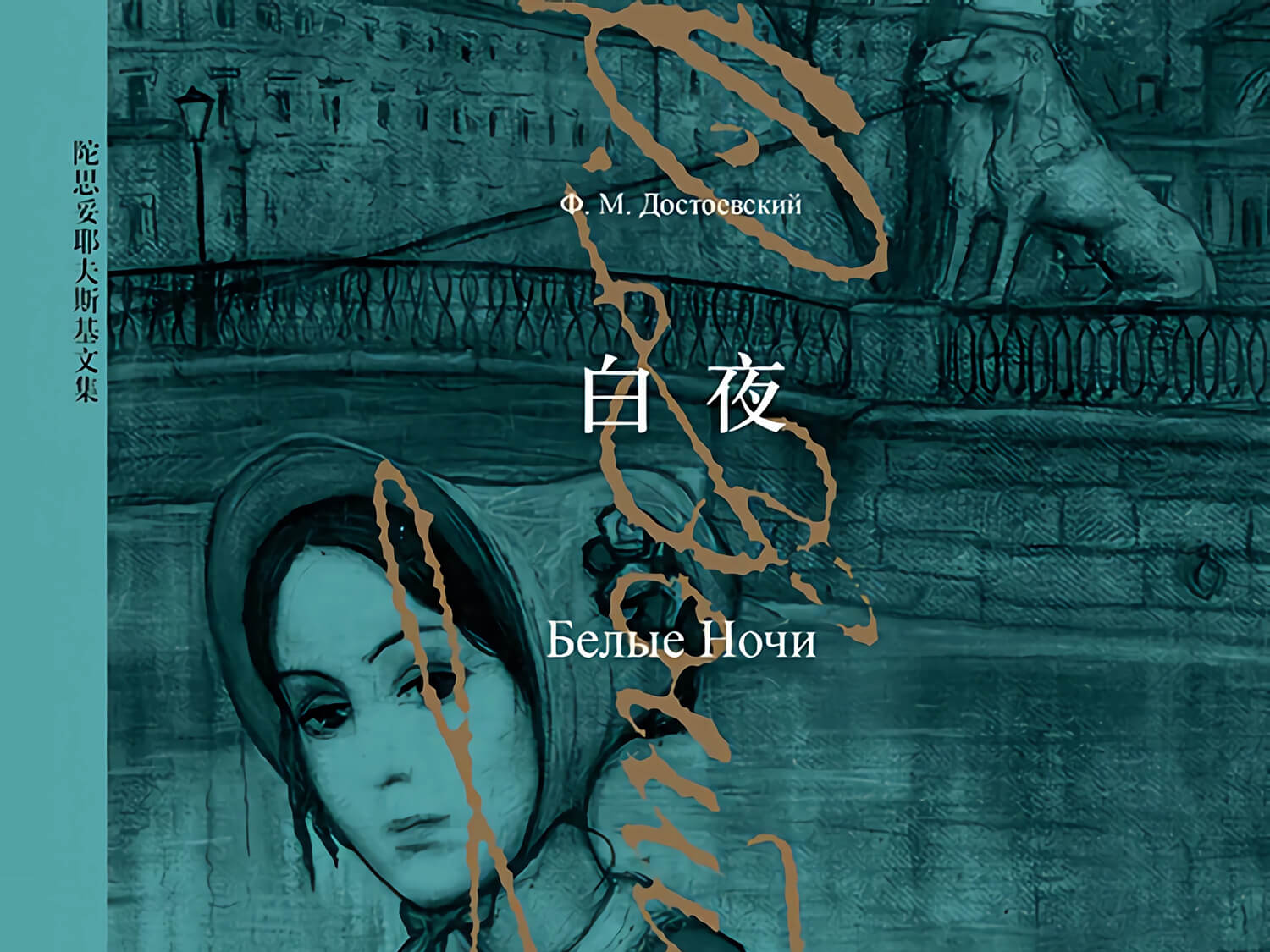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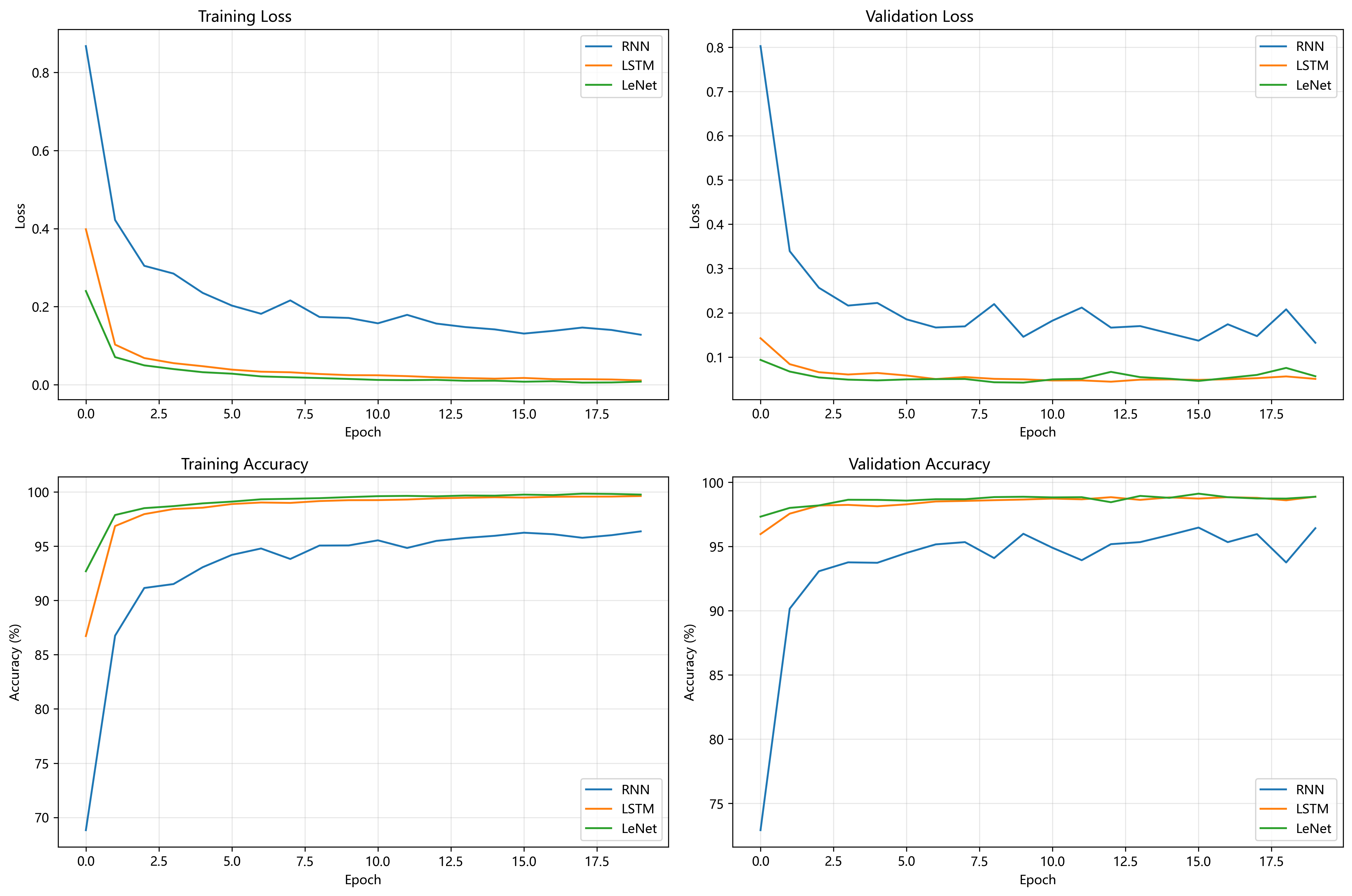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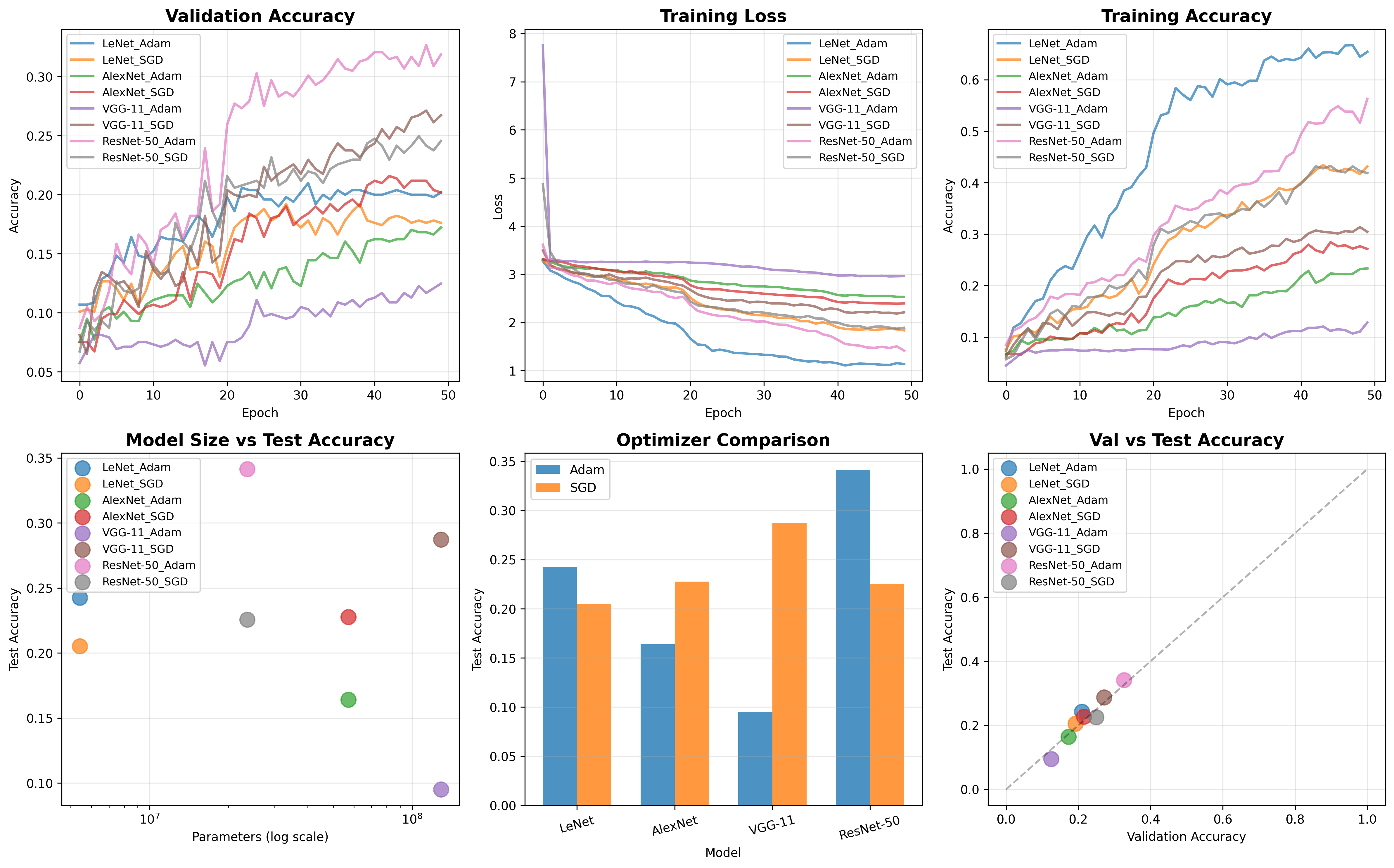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