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通过临床实践揭示了精神病治疗的本质:必须深入患者未被言说的个人生命叙事,而非停留于症状表象。他强调,每个异常行为背后都潜藏着未被理解的人格矛盾与生活史,治疗需以整体人格为对象,通过梦境分析、共情对话唤醒潜意识中的原型意象。在与患者深度互动中,荣格发现了集体潜意识的存在,这种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使他意识到”万物同理”的古老智慧。他提出阿尼玛/阿尼姆斯理论,认为男女潜意识中存在着互补的异性原型。面对精神探索的孤独,荣格坦言被创造性”魔鬼”驱使,这种内在张力既成就了他的学术突破,也造成人际疏离。晚年的他辩证看待存在本质:世界是野蛮与圣洁的共生体,生命在有限与无限的交织中显现意义。承认人性的局限,恰是与万物建立深层联结的起点,正如老子所言”俗人昭昭,我独昏昏”,智慧始于对未知的敬畏。
那时候,这些便是我开始自己的精神病学研究生涯时的状况。我的客观生活得以从主观实验中产生出来。我既没有超越自我并以真正客观的方式来观自身命运的渴望,也没有这种能力。我乐于去编织一个事情原本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幻想,或者犯一种人所熟知的错误,写一部为自己辩解的书。总而言之,人是一个事件,它无法自觉地判断自己。无论它是好还是坏,都得由其他人来做出这种判断。
在许多情况下,精神病人就诊的时候通常都有一个没人知道,而他自己也没有说出来的故事。我认为,真正的治疗,是从对这种完全属于病人个人的故事进行调查开始的。这故事是病人心里的秘密,是把他摔得头破血流的岩石。如果我知道了这个隐秘的故事,那也就意味着我已经掌握了治疗的关键。医生的职责就是想办法找到这个关键的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只是探讨意识方面的音息还远远不够。有时候,进行联想试验则有可能是一个找到这种方法的途径。分析病人的梦境,或抱着同理心,耐心地与病人进行长期接触也会达到同样的效果。要对病人进行治疗,必定要从病人的整体人格着手,而绝不是只考虑症状。我们必须深入整体的人格问题。
在精神病的种种表现背后,其实潜藏着一种人格、一部生活史、一种希望与欲望的形式。如果我们不了解它们,那么是我们做错了。这时候,我第一次明白,人格的一般性的心理,是隐藏在精神病的症状之中的。我们甚至在其中遭遇到了,人类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这种矛盾与冲突是过去就已经有的。尽管病人可能显得麻木不仁和悲怆,或者看起来完全就像一个白痴,但是他们的思维活动却仍然非常活跃,而有意义的事物,比它看起来的更有意义。从本质上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精神病有什么新鲜的和完全不为人所了解的地方。相反,我们遇到的是他们自已的本性。
这次体验是一次真正的同时发生的现象,这种现象通常可以在与一种重大的情境(比如死亡)有联系的情况下观察得到。通过潜意识中的这种时空的相关或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已经觉察出了正在其他的地方发生着的事情。集体潜意识是所有人共有的意识,也是古人所谓的“万物同理”的基础。在上述那种情况下我的潜意识其实是了解那位病人的状况的。实际上,那天一整晚,我一直感到莫名的不安与神经紧张,这种情绪与我平时的情况正好相反。
在与病人的接触中,在与各种心灵现象接触的过程中,我眼前出现了大量这类现象。从中我也学到了很多,不仅包括知识,还包括洞悉自己本性的能力,而这点也更为重要。犯了很多错,经历了许多失败之后,我汲取了比较多的经验教训,我的病人大部分是女性,她们往往有着超凡的自觉性、理解力和聪明才智。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于她们的加入与配合,我才有可能开辟各种新的治疗途径。
我的一些病人后来成为我的学生,真心诚意地跟着我学习精神治疗,并把我的观念传播到了全世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走过了几十年的风雨。
得益于这些病人,我才有机会深入了解现实的人生,并从他们身上理解到了真谛。在我看来,与其跟名人们泛泛而谈,不如与我那些病人深入打交道,因为他们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心理状况差异极大,相比之下,他们的有着无可匹敌的重要性与那些不知名的人们的交谈,恰恰是我一生中所有过的最美好和最有意义的谈话。
当我把各种情感变成了意象,换句话说,就是发现了掩藏在这些情感之中的意象之后,我内心逐渐变得平和。如果我让这些意象继续潜藏在情感中而不被发现,那么我很有可能被它们撕个粉碎。我只有一次成功的机会,能够把它们一个个分离出来。但如果是这样,我就会无可避免地变成精神病人,并最终被它们毁掉。我从自己的实验里得知,从治疗的观点来看,它有助于找到潜藏在情感背后的特定意象。
一个女人竟从我心里冒出来干扰我,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极大的兴趣。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她一定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我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赋予灵魂以“阿尼玛”的名字,为什么会把它设想成是女性呢?后来我逐渐明白了,在男人的潜意识中,这个内心的女性形象起到了一种典型的或原型性的作用,因此我把她称为“阿尼玛”。同样,在女人的潜意识中也存在着相对应的形象,我称它为“男性意向”。
如果没有这个幻觉,我很可能失去方向,而且不得不放弃命中注定要从事的事业了。但是在梦里,它的含义已经被清楚揭示出来了。在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正一头扎进了那个未知的世界之中了。那是弗洛伊德学说以外的世界,尽管我对它一无所知,但仍然义无反顾地向着黑暗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当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接着又做了那样一个梦的时候,我很难不把它看作是一种天意。
我花了足足四十五年的时间,对自己所体验到的并记录下来的各种事情进行思考与提炼,就像把它们装在科学器皿里蒸馏一样。年轻的时候,我的目标一直是要在科学领域取得一番成就。但是随即,我又接触到了这股熔岩,它的炽热又重新改造了我的生活。促使我去研究它,它是一种本质,而我的著作便是这种闪光点与当下的成功尝试相结合的结果。
我追溯内心那些意象的岁月,正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所有根本性的素材得以确定。一切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后来的细节和详情不过是这一根本性的素材的补充和详述而已。这些素材是从潜意识中爆发出来的,而且一开始就把我彻底淹没了。这些素材就是“原始素材”,值得人付出一生去研究。
但是,只有当我们与极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能获得对无限的感知。人的极限就是“自性”,它表现在这样的体验中,即“我只是这样的”。对于我们狭隘地局限于自性这一情况的意识,是构成与潜意识的无限性之间联系的唯一原因。这种认识会使我们感觉到自己既是有限的,同时又是无限的,既是此又是彼。只要意识到自己在我们个人的组合体(最终是有限的)中的独特性,我们就有能力意识到无限。
在一个只专注于扩张生存空间,以及为了掌握理性知识而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时代,要求人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和自己的局限性,本身就是对人提出的一种最高级别的挑战。独特性和局限性是同义词。没有它们,我们就不可能感受到无限,自然也就不可能达到意识,而只能形成一种对它的幻影般的认同,表现形式是醉心于使自己成为多数派,以及贪婪地追求政治权力。
我们的时代把所有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此地此刻,因此造成人以及人类世界的妖魔化。独裁者的出现,带来了众多灾难,这些现象都源于超级知识分子因为目光短浅而剥夺了人的超越感。其他人也像他们一样,变成了潜意识的牺牲品。但是,人类所应完成的任务却恰恰相反,即认识到潜意识往外喷发的内容。人既不应该坚持自己的潜意识,也不应该与自身存在的潜意识因素同化,进而回避自己的命运,也就是创造越来越多的意识。从我们的认知来看,人类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普遍存在的黑暗之中点起火光。甚至可以假设,与潜意识会影响我们一样,我们的意识的增长同样也会影响潜意识。
我无法接受人们夸赞我聪明或说我是个圣人。一个人曾从一条溪流中舀取了帽子的水,这能有多少呢?我并不是那溪流,而只是站在溪边的人,然而我却什么也没做。其他人也站在同一条溪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发现自己得对这条溪流做点儿什么。我却没有做任何事。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那种必须注意到樱桃是长在花梗上的人。我站着并观看着,赞美着造化的变化无穷。
我和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在于:那“起间隔作用的墙壁”在我眼里是透明的。这也是我与众不同的地方。别人发现这些墙是不透明的,他们根本看不见墙后的东西,所以就认为后面什么都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我能够觉察到有的事情在看不见的地方正在发生着,因此我内心具有一种确然性。这种确然性是那些什么都看不见的人所没有的,他们也无法作出结论,即便给出了,也不敢相信。我不知道是什么使我开始觉察到了生活之流的。很有可能是潜意识本身,也有可能是我早年时所做的各种梦,它们从一开始就为我指明了方向。
能够认识到隐藏在背后的各种过程,很早就对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产生了影响。这种关系无论在我童年时期,还是今天,基本上都一样。我觉得自己的孩提时代是孤独的,成年后,直到现在仍然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并且还暗示一些事情,然而其他人显然完全不了解这些事,或者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想知道。孤独并不是因为我周围没有人,而是由于我无法把自认为是重要的事情与其他人进行交流,或是因为保留某些别人无法容忍的观点。从我早年对各种梦的体验开始,孤独就一直伴随着我。当我对潜意识进行研究时,这种孤独感达到了高峰。一个人如果懂得比别人多,那么他就很容易变得孤独起来。但孤独并不一定会妨碍友谊,因为没有谁比孤独的人对友谊的体察更加敏感。只有在每一个人都记住了自己的个性,避免使自己混同于其他人时,友谊才能与日俱增。
拥有一种秘密,拥有一种对未知事物的预知性,很重要。它使生活具有了某种非人格化的东西,充满了神秘。一个人如果从未体验过它,就等于错过了某种重要的事情。他必须认识到,从某些方面来看,自己生活在一个神秘的世界里;必须感觉到,发生了某些他能够体验到却无法解释的事情;必须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一切并不是都可以预见的。这个世界里有很多让人料想不到的事物,也有很多让人难以置信的事物。只有感觉到这些,生活才是完整的。从一开始,我就觉到这个世界是无穷的,而且是无法把握的。
在与我的观念共存方面,我曾遇到了许多麻烦。我身上有一个魔鬼,最后证明它的存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压倒了我,如果我有时竟然拒绝,表现得无情。那是因为我被这个魔鬼控制住了。任何到手的东西,我都不会感到满意,而是急忙又转移到其他事物上去,急于追逐我的幻觉。由于我同时代的人根本无法领悟我的幻觉的意义,所以,可以理解,他们所看见的只是一个匆匆赶路的傻瓜。
我得罪过许多人,因为一旦看出他们并不理解我,那么对于我来说,事情就结束了,我还得继续向前。我对人缺乏耐心,但对我的病人例外。我不得不服从于内心的法则,它强加给我,并使我没有选择的自由。当然,我并不总是服从于它的。一个人的行事如果并不连贯,那么他又将怎样处世呢?
如果有人能够与我的内心世界产生关联,那么我就会不断地出现在他们身边,而且跟他们交往密切。但是之后,可能又会发生我与他们分手的情形,原因是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消失了。我只好痛苦地认识到,人们依然继续存在,甚至在他们再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跟我说的时候仍然一样。许多人在我身上激起了活动着的人格的感觉,但前提只是他们出现在心理学的曼陀罗之内。不久,当聚光灯照到了其他地方的时候,就什么也看不见了。许多人都可能引起我强烈的兴趣,然而我一旦完全了解了他们,那吸引我的魔力就消失了。正因为如此,我树敌很多。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往往缺乏控制住自己生命的能量。他并不是自由的,他不过是被自己身上的那个魔鬼所驱赶着的俘虏。
一种强大的力,
可耻地把我们的心夺走,
因为天神个个要人献祭:
谁如果拒绝上供,
谁就难得善终。
这是荷尔德林说的。缺乏这种自由,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形,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战场上一样,最后说着:“我亲爱的伙伴,现在您倒下了,我却必须继续前进”,因为“一种强大的力可耻地把我们的心夺走”,“我喜欢您,我确实爱您,可是我不能止步不前”。这确实让人感伤,而我自己就是那个牺牲品,我不能止步不前。魔鬼掌管着所有的事情,让人一一经历,而且受到福佑的不一致性在悉心照顾。与我的“不忠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却能够将信仰保持在毫不令人怀疑的程度上。
或许我可以说:我比其他人需要人的程度更高,但同时我又不怎么需要人。当这魔鬼在起作用时,我难免做事过火,或者不及。只有当它蛰伏的时候,我才能达到中庸的态度。
这个魔鬼具有创造性,他随心所欲地操控着我。一般的事情,尽管我计划周详,最后却常常落得个最坏的结局,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这样,也不是每一次都这样。我觉得,为了求得补偿,我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我从祖父的烟叶壶里取出烟叶,装满了我的烟斗。我还保存着他那根登山手杖,这手杖的顶端镶着一只羚羊角,那是他从蓬特雷西纳带回来的,当时那里刚开设一个疗养地,他是首批客人之一,获得了这个纪念品。
我对自己一生所走过的历程感到满意,我的生活很充实,并使我获益良多。我本来根本不敢指望会有如此大的收获。但让我感到意外的事情常常发生。我想自己如果是一个不同的人,或许很多事情就会有所不同了。但是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就是我。很多事情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产生了结果,不过最后这一切并不是都对我有所助益。但是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自然地发展的,就像注定了一样。我后悔由于自己的固执而做了许多蠢事,但如果没有这种气质,我却又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我既感到失望又不失望。我对其他人失望,对自己失望。我从其他人那里学到了许多令人惊异的本领,取得了超越自己期许的成就。我无法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生命现象和人的现象所包含的内容实在太过广泛。年龄越老,我所懂得的就越少,对自己本身的洞察或了解也越少。
我对自己感到吃惊、失望,同时又感到欣慰。我既沮丧、消沉,同时又充满喜悦。所有这些感觉不多也不少地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无法作出有价值或没有价值的终极性判断。我也无法对我本人以及自己的一生,作出一个结论。没有什么事情是我所确信无疑的。我也没有什么明显不变的看法,我的确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不变的看法。我只知道自己来到这世上,并存在着,而且感觉自己是被裹挟者向前的。我存在于某种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的基础之上。尽管存在着所有这一切的不确定性,但我却感觉到了所有的存在都潜藏着一种稳固与实在性,而我的存在方式则有一种连续性。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野蛮而又残忍的世界,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圣洁的美的世界。我们认为哪一种成分更重要,它是有意义的,抑或是无意义的,如果无意义性占据了绝对优势,那么生活的意义性就会随着我们发展的每一步而逐渐消逝。但我认为,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就像所有形而上学的问题一样,或许这两者都是正确的:生活既是有意义的,又是没有意义的。但我却抱着这样的期望:有意义将占上风并将战胜无意义。
老子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这就是我在高龄的感觉。高瞻远瞩,对是否有价值亲身经历、深有体会,在人生的终点想要回归自己的生存方式,复返永恒莫辨的意义,老子就是例证。见多识广的老者原型永远名实相符,这种典型人物显现于智慧的每个阶段,无论是老农还是如老子这样的圣哲,都认同自己。老年就是这般光景,也就是局限,不过,还有许多事让我充实:植物、动物、云彩、日夜还有人身上的永恒。对自己越无把握,与万物的亲近感就越强。对,我觉得让自己与世界如此长久隔离的那种疏离迁入我的内心世界,意外地揭示出我不自识。
![图片[1]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阅读】《荣格自传》各章节个人摘录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小竹の笔记本](https://img.smallbamboo.cn/i/2025/05/12/682211c9a3b9d.jpg)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20684/
说明:本文每一行均为部分摘录,阅读连贯性可能较差,个人存档用,推荐购买正版书籍阅读。
2. 论文总结类文章中涉及的图表、数据等素材,版权归原出版商及论文作者所有,仅为学术交流目的引用;若相关权利人认为存在侵权,请联系本网站删除,联系方式:i@smallbamboo.cn。
3. 违反上述声明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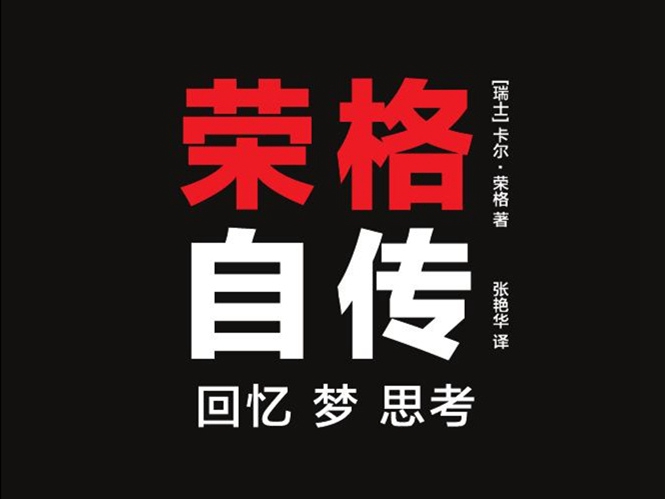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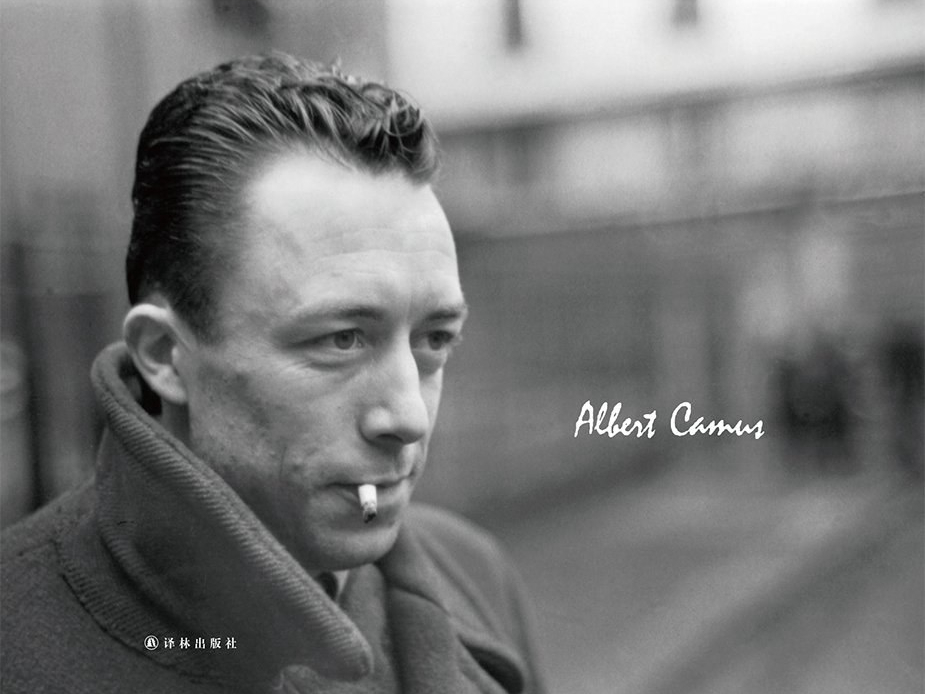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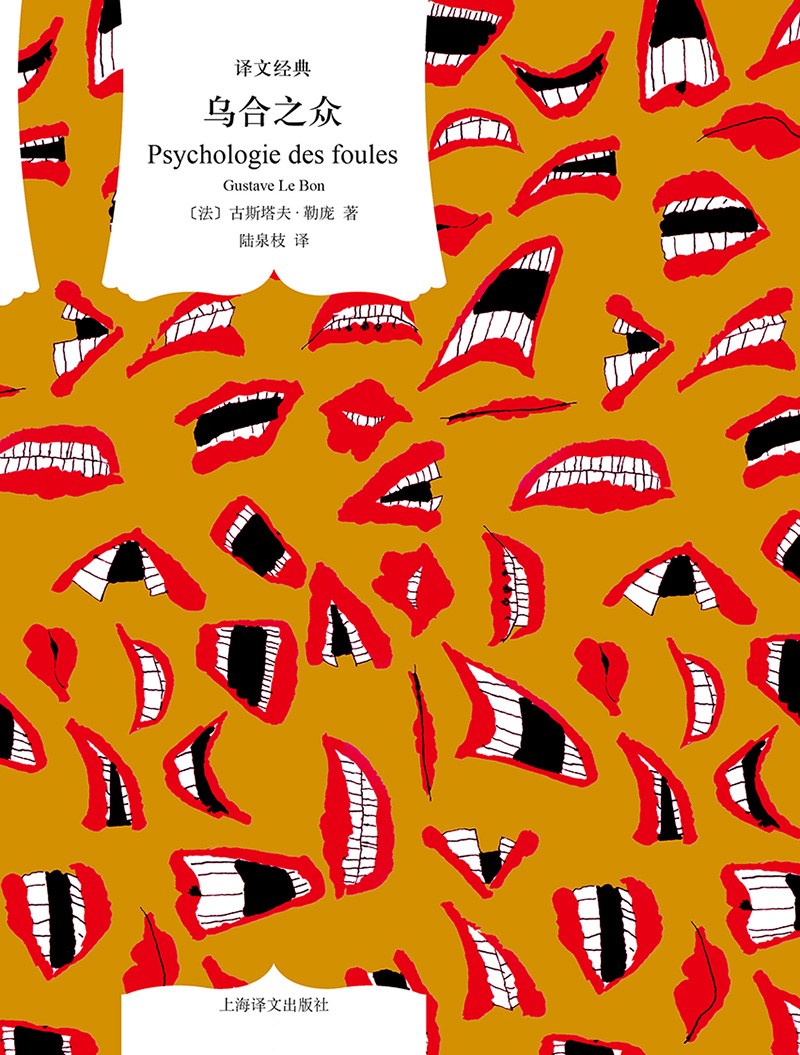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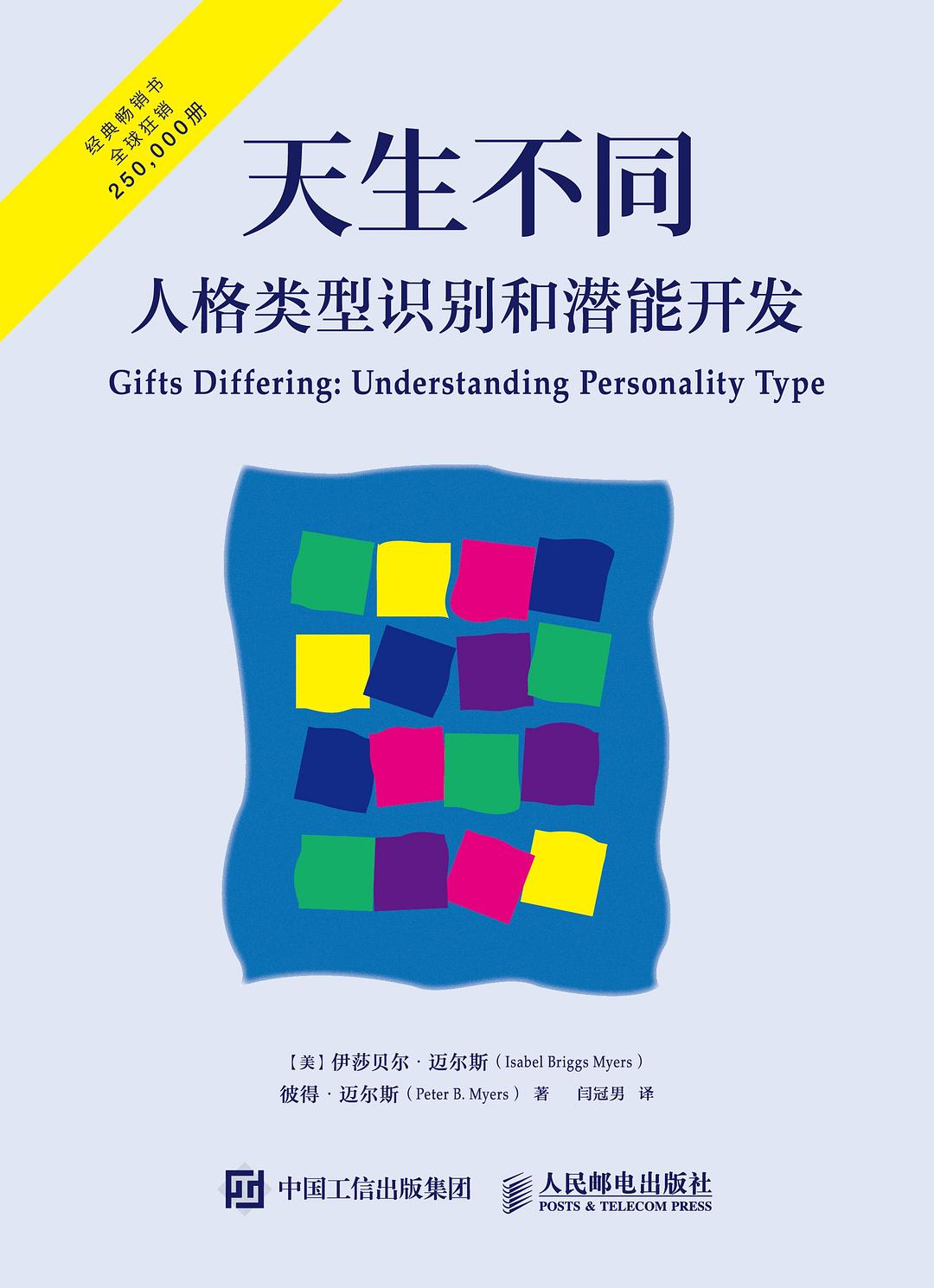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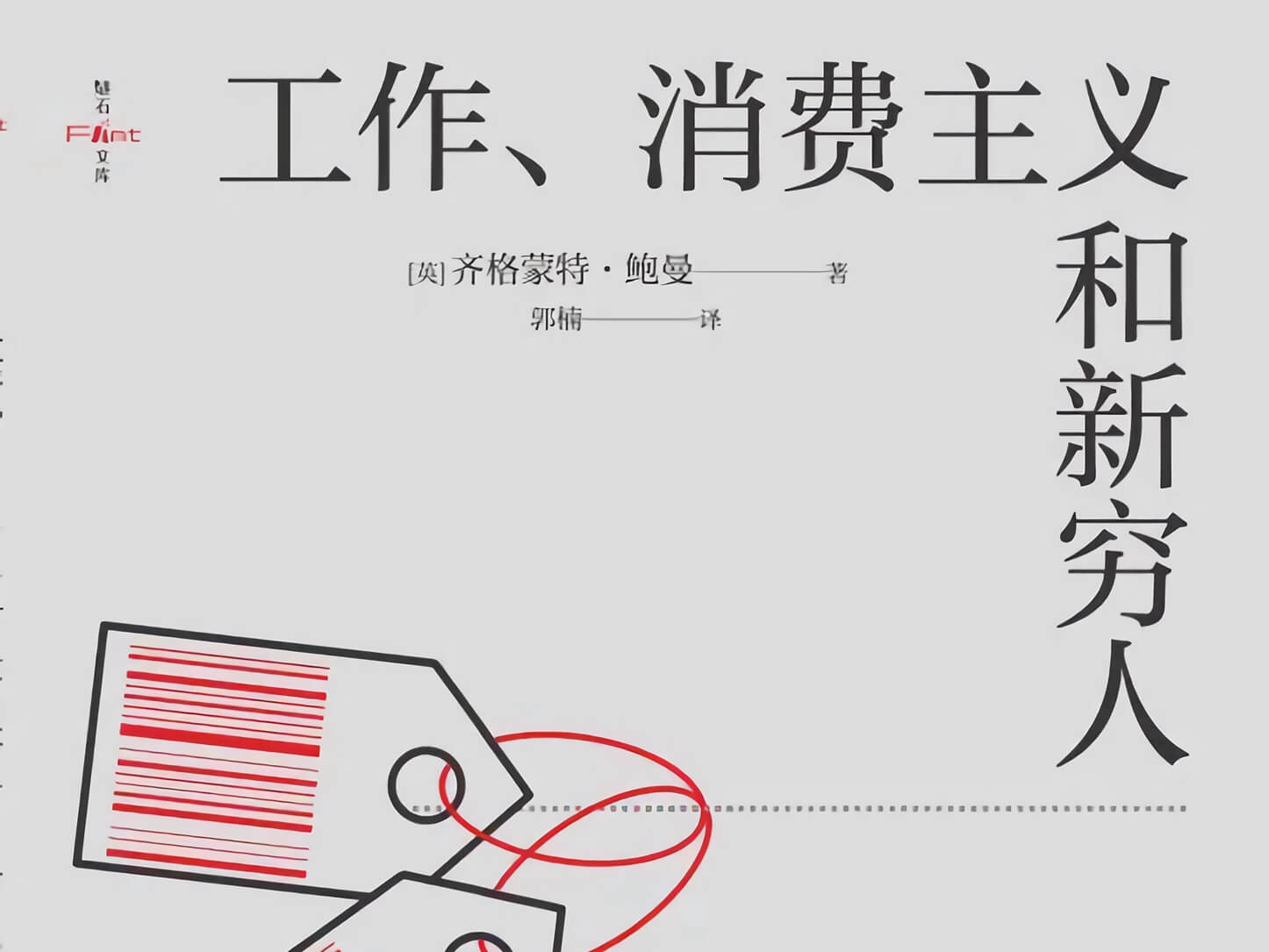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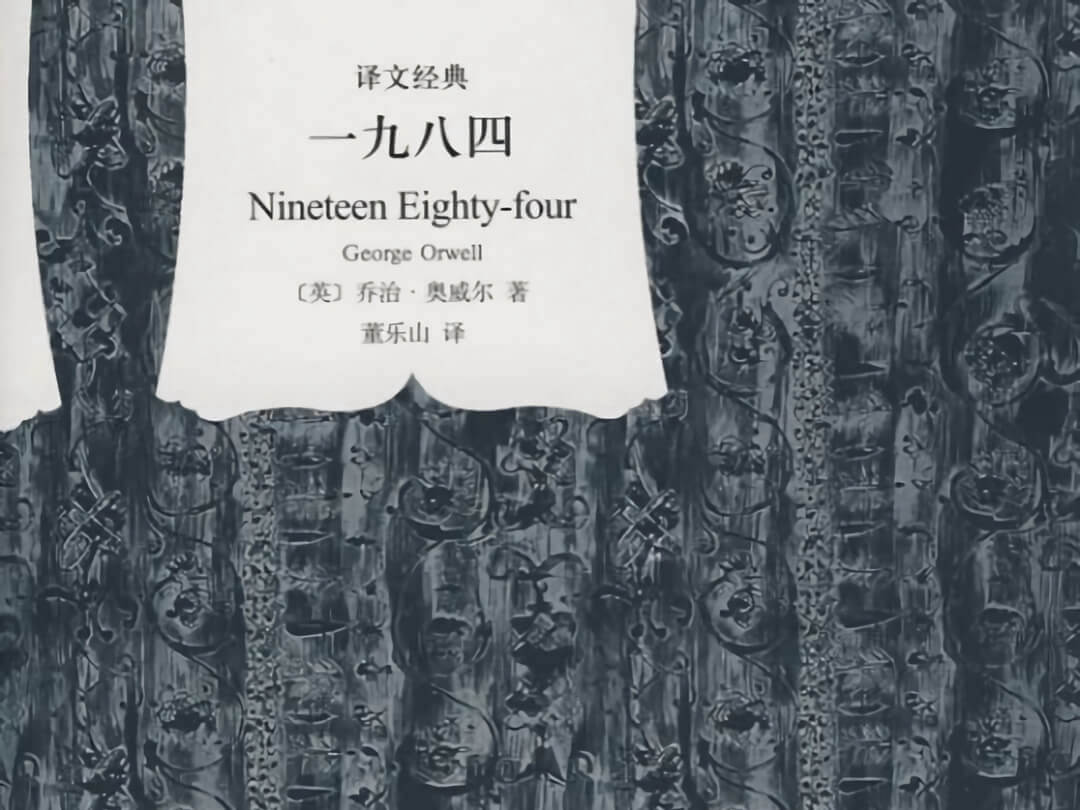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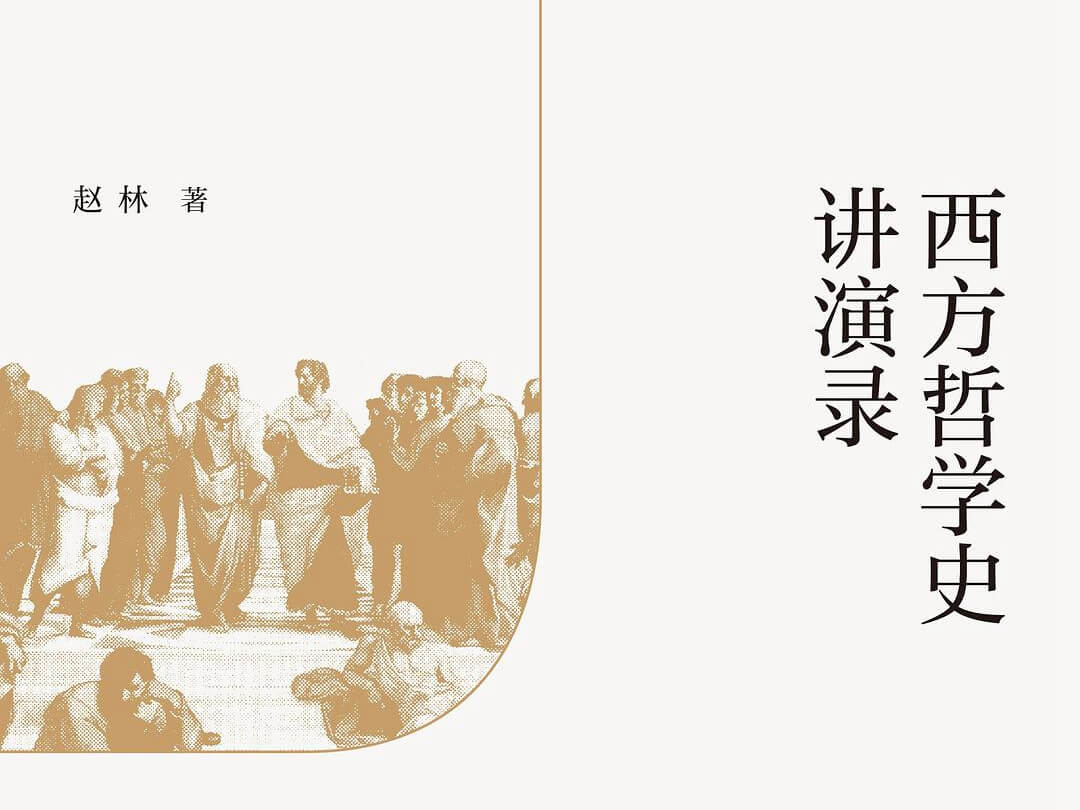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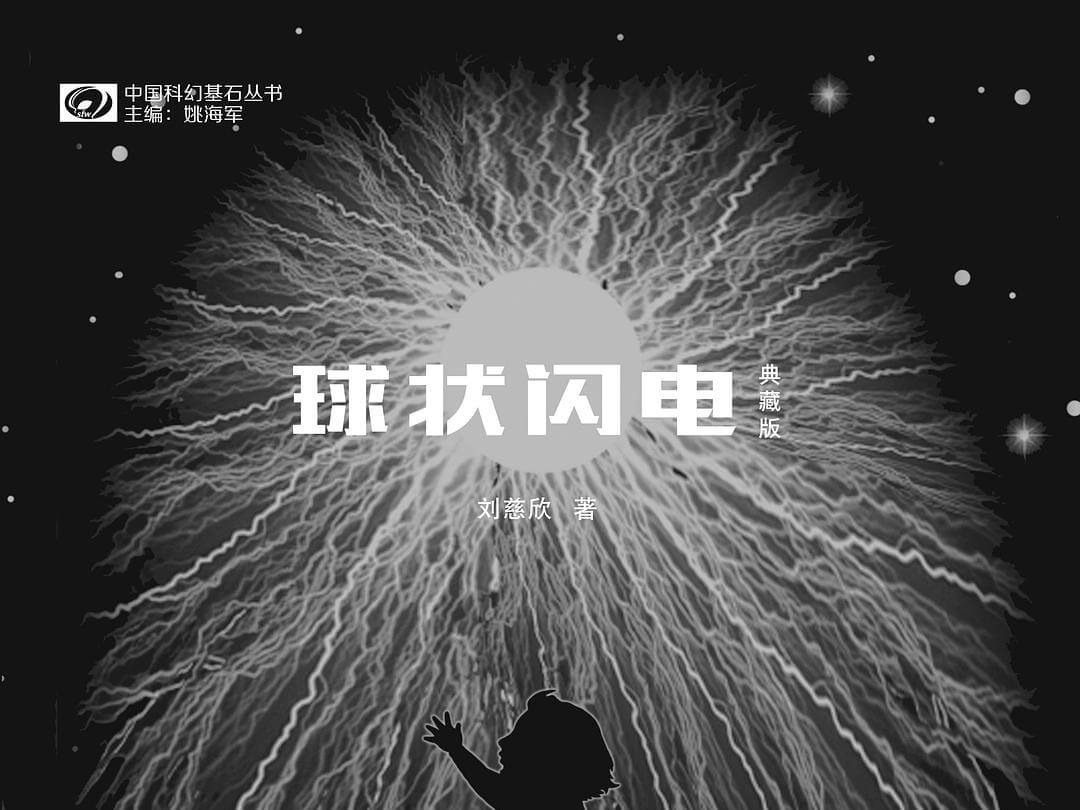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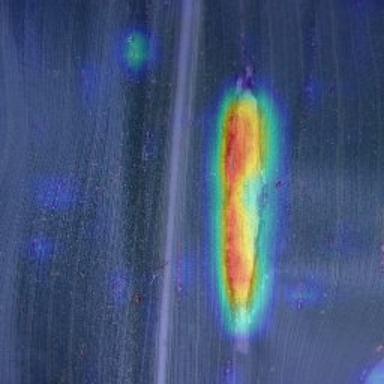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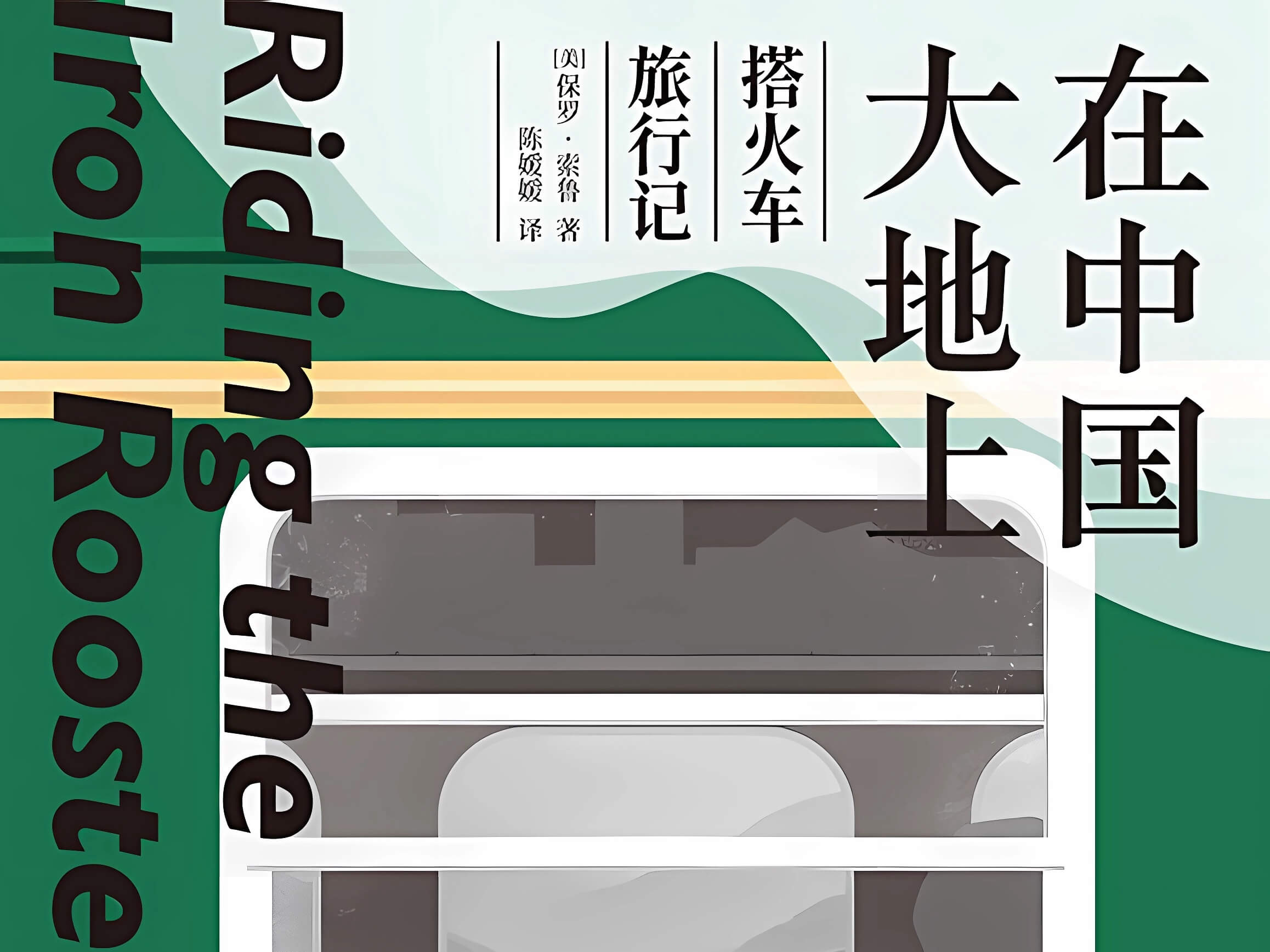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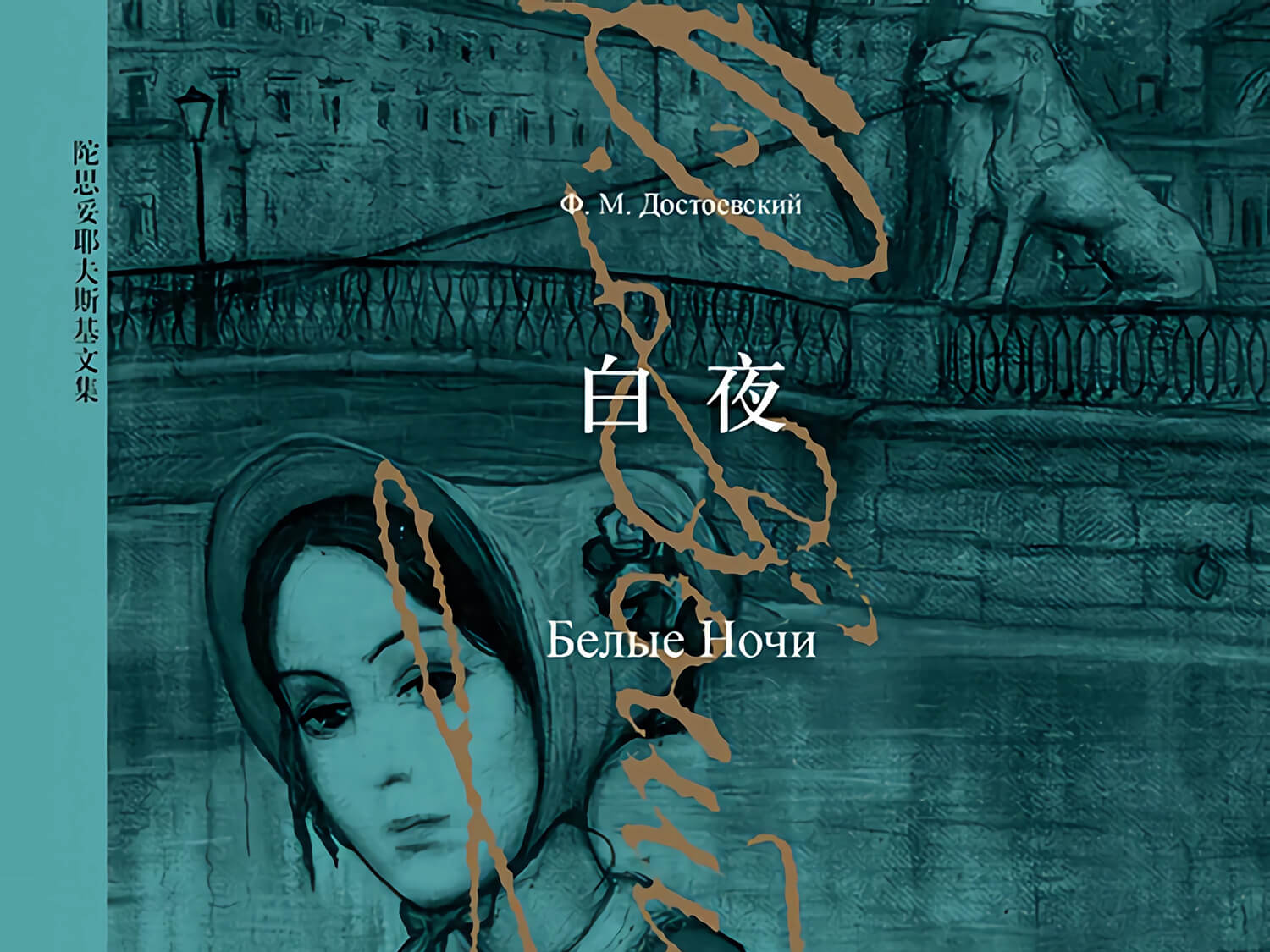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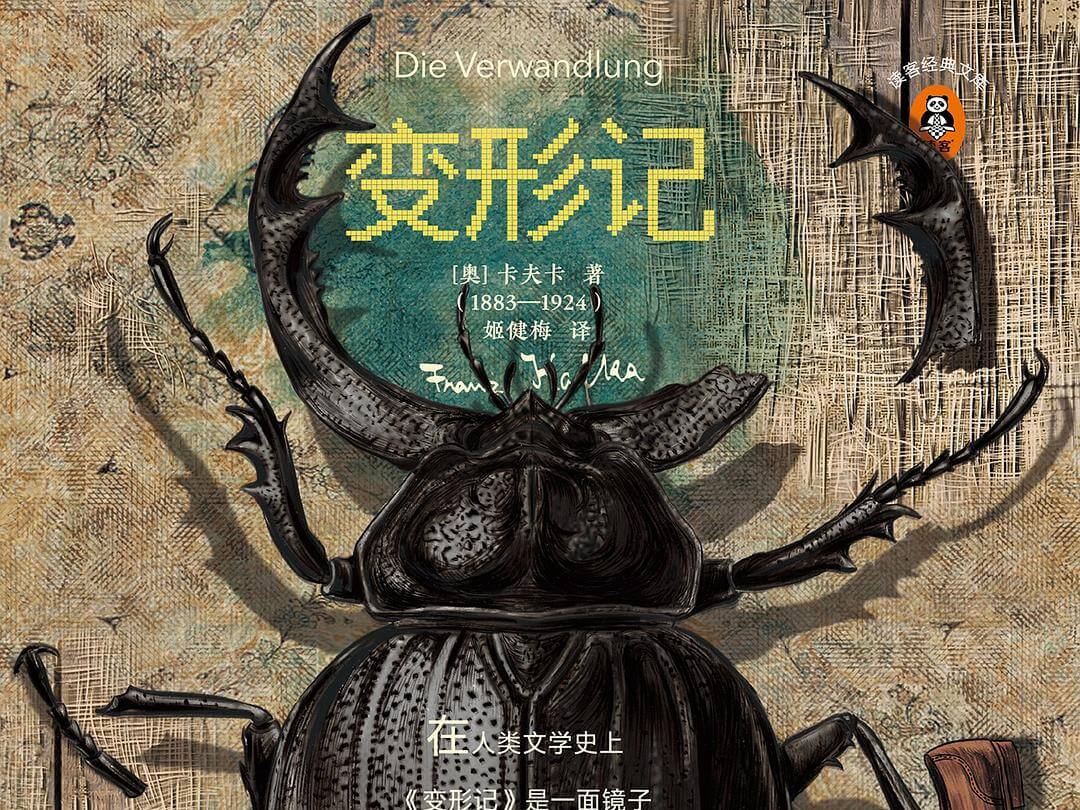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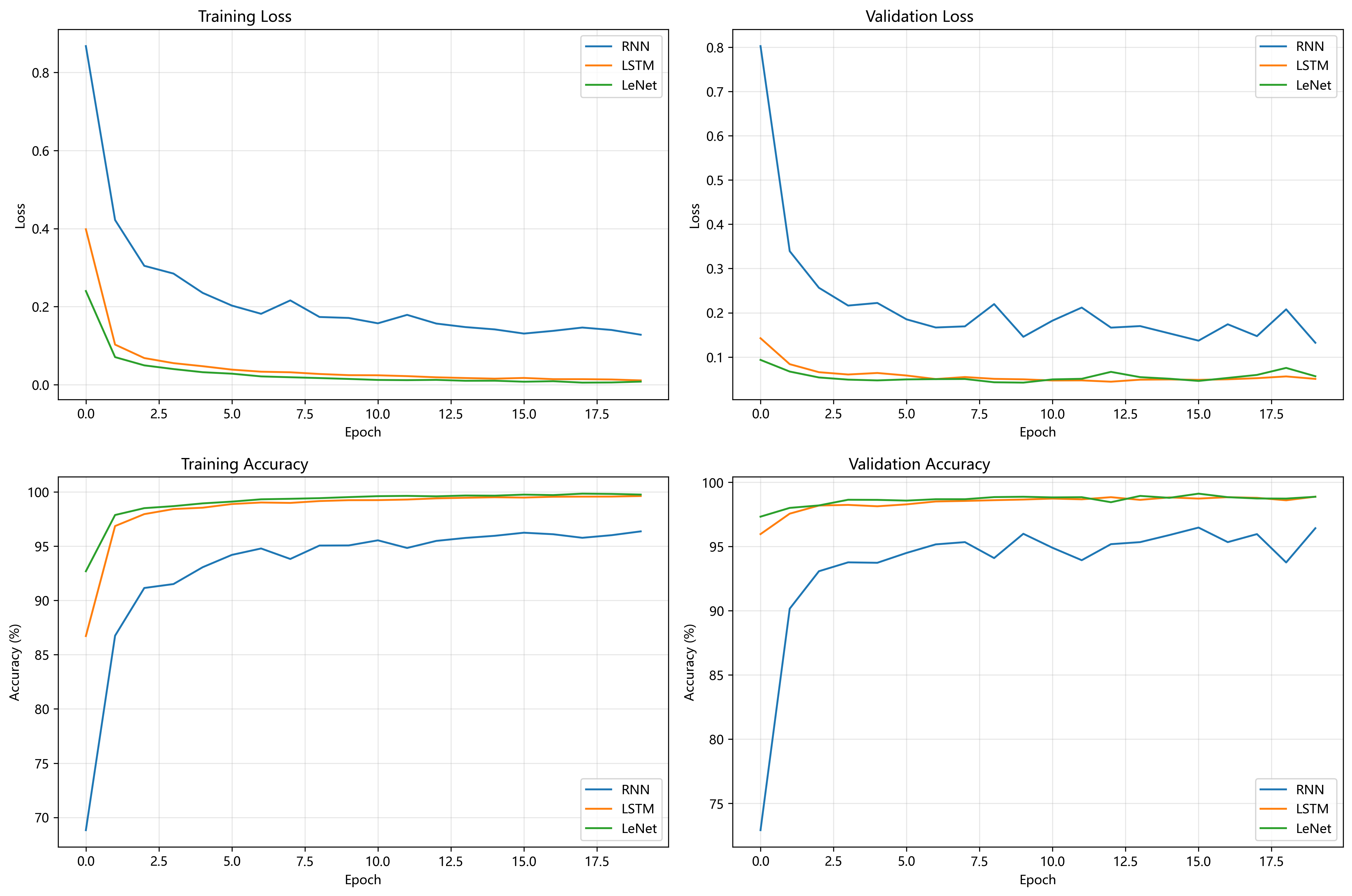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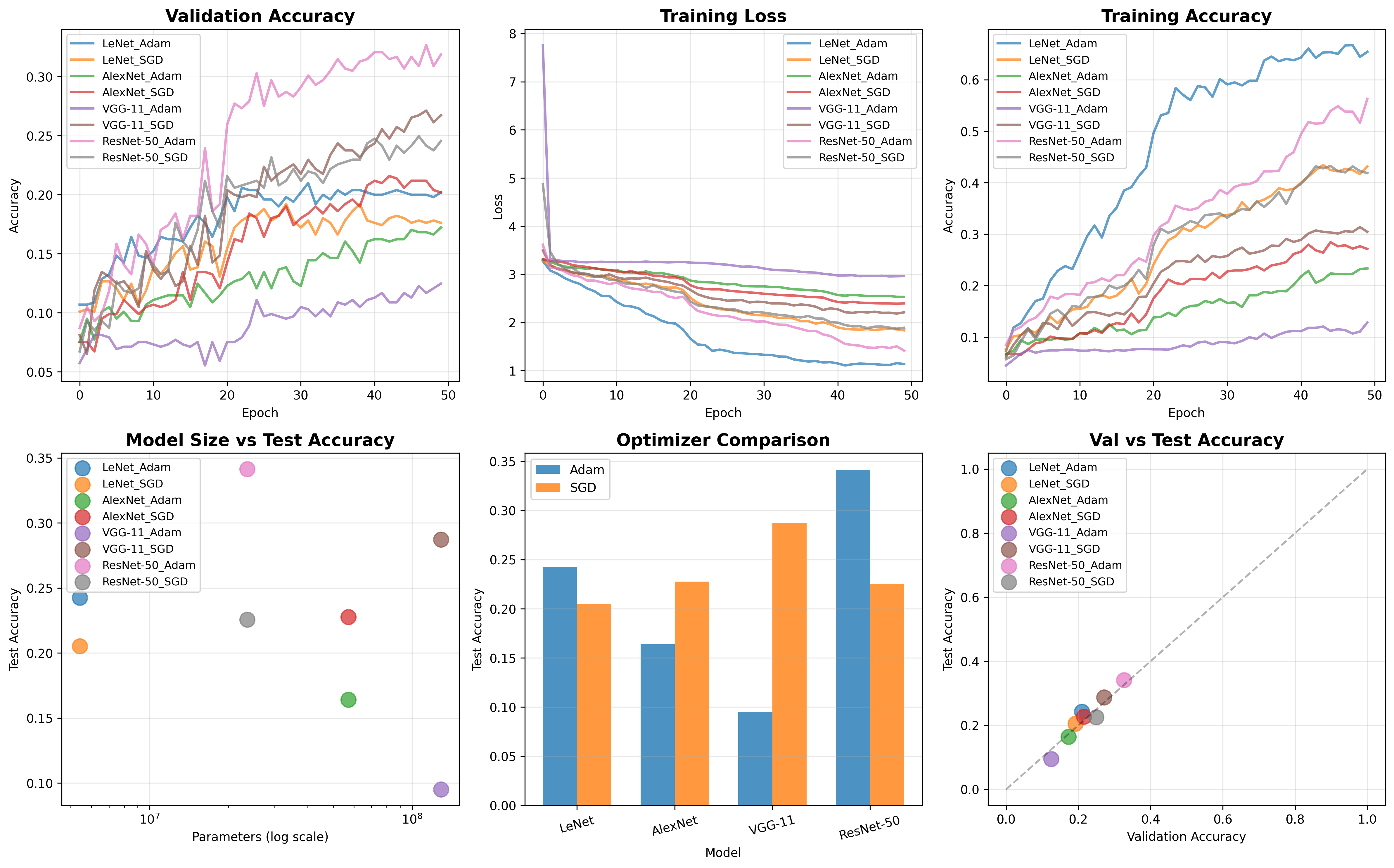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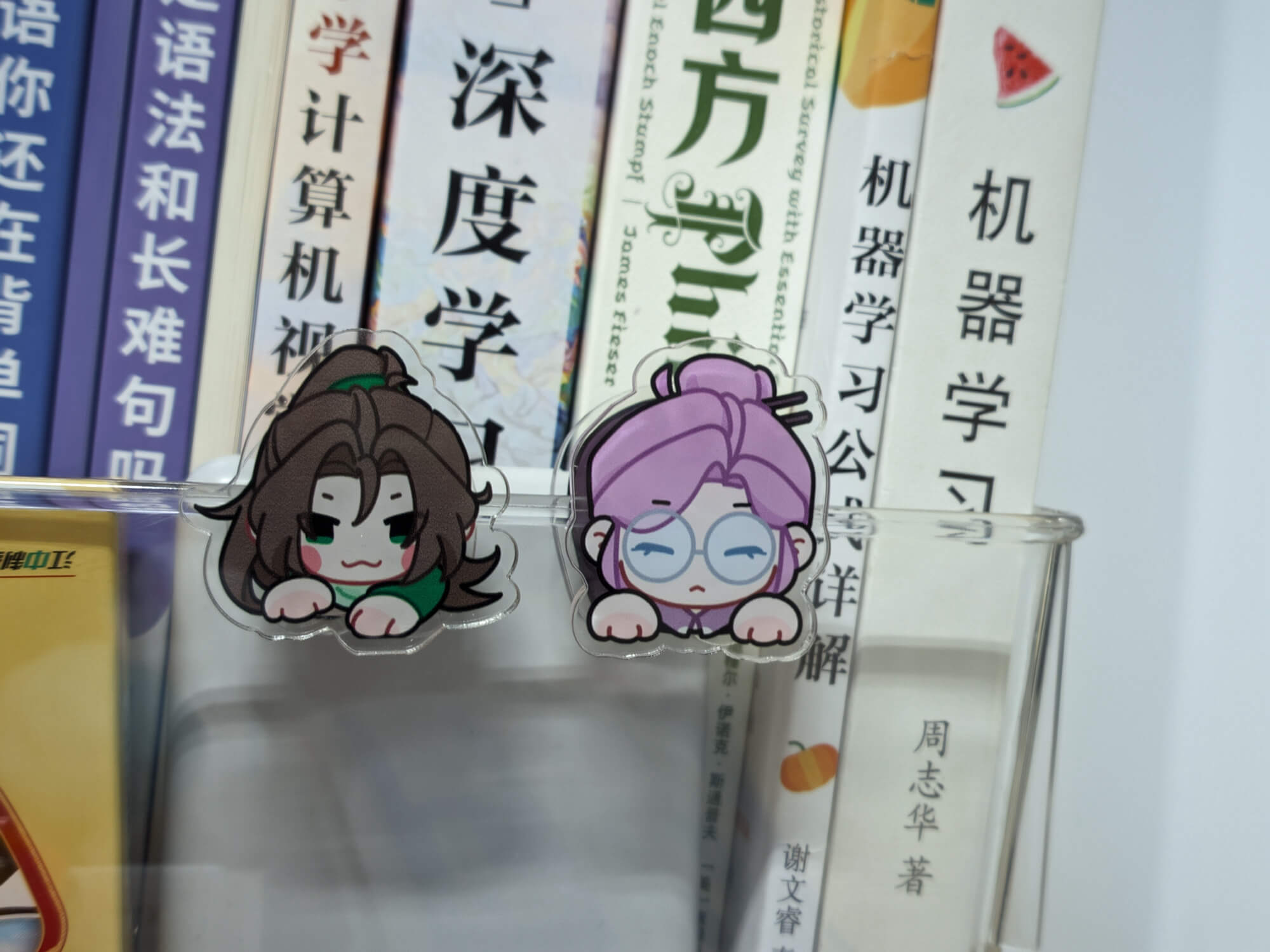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