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
近代认识论,无论是唯理论还是经验论,都力图追求真理性的知识,而真理性的知识就是指那种既具有普遍必然性、又能够不断进行内容更新和拓展的科学知识。
经验论只是执着于那个无可怀疑的起点,但是却达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而唯理论者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他们的方法是一种理性演绎法。他们认为知识的开端不是感觉经验,而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从这些天赋观念出发,遵循一套严格的形式逻辑演绎规则,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建构起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系统。这就是唯理论的基本路线。
与经验论的问题不同,唯理论的致命弱点有两个。第一,作为整个演绎起点或前提的天赋观念本身的合理性何在?它是靠什么东西来保证的?这个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因此天赋观念学说遭到了经验论者的猛烈批判。第二,即便我们承认有天赋观念,也承认那一套形式逻辑演绎系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后这种从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出发、按照形式逻辑演绎规则不断推理的做法能够给我们的知识系统带来什么新内容呢?按照唯理论的观点,关于客观对象的感觉经验完全是多余的,而且是错误的根源,因此一个人只须关起门来,从天赋观念出发,遵循形式逻辑不断地推演,就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这显然也是一个很荒唐的结论。如果说经验论发展到最后,演变为一种否定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怀疑论,那么唯理论发展到最后,则演变为一种否定科学知识的经验内容的独断论。
笛卡尔哲学与唯理论的开端
唯理论的主要哲学家有三位,即笛卡尔、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其间我还要穿插讲到伽桑狄和马勒伯朗士这两位哲学家。
唯理论的创始人是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他是17世纪欧洲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评价道,每一个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奇特习惯,苏格拉底喜欢光着脚站在冰天雪地里思考问题,而笛卡尔则喜欢在温暖的壁炉里进行他的哲学沉思。
如果说16世纪是一个虔诚信仰的时代,那么17世纪就是一个普遍怀疑的时代,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构成了17世纪的时代精神。近代知识论也是从怀疑开始的,在这一点上,唯理论与经验论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笛卡尔却认为,真理的标准就是清楚明白,凡是不够清楚明白的东西,都应该进行怀疑。感觉经验只要欺骗过我们一次,它就不是清楚明白的,就要受到怀疑。因此我无法根据感觉经验来断定我是真的坐在火炉边,还是梦见自己坐在火炉边。
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进行了怀疑之后,笛卡尔又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了怀疑。他说,有时候我做梦梦见自己没有身体;再比如说,有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但是到了天阴寒冷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感觉到腿疼,这不就证明了身体可能也是虚幻的吗?
最后,像逻辑学、数学这一类的东西,比如“一加一等于二”等公理或定理,也同样可能是假的。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一个恶作剧的上帝,他老是诱导我们犯同样的错误,从而得出“一加一等于二”这样的普遍公理。由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我们相信自己所怀疑的那些对象是确切无误的,所以,一切事物都值得怀疑。这样,笛卡尔就把普遍怀疑当作了自己哲学的出发点。
在进行了普遍怀疑之后,笛卡尔表示,当我对所有的事物都进行了怀疑之后,却发现有一个东西是不能怀疑的,那就是怀疑本身。也就是说,我正在进行怀疑,这个事实本身是不能怀疑的。
于是,笛卡尔就得出了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那就是“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因果假定之上的,即凡思想必有一个思想者,因此从作为结果的“思”就推出了作为原因的“我”。但是,这种推论后来遭到了休谟和康德等人的质疑,再往后又遭到了胡塞尔、萨特等人的批判。他们都指出,对怀疑活动的自觉是一种内心的反省,属于一种内在经验,这种内在的经验事实是不可怀疑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笛卡尔的怀疑与古代怀疑论者的怀疑是不一样的。对于古代怀疑论者来说,怀疑本身就是目的,而笛卡尔的怀疑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找出那个不可怀疑的东西。
为了实现从自我到上帝的飞跃,笛卡尔再次借用了安瑟尔谟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笛卡尔说道,当我在进行怀疑的时候,我立刻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完满的东西,因为我在怀疑,怀疑相对于确定来说就是一种不完满性。而我之所以知道自己是不完满的,是因为我心中有一个完满的东西,这个完满的东西就是上帝。
笛卡尔强调,正是由于我心中有一个无限完满的上帝观念,我才能够知道自己是不完满的。而这个上帝,既然是无限完满的,他就不可能仅仅只存在于我的心中而不同时具有客观的存在,因此在上帝这个无限完满的东西的概念中就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存在。
上帝作为全知全能全善的创造者,他肯定不会欺骗我们,他保证了他所创造的两个世界的真实性,这两个世界就是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笛卡尔把精神和物质都叫作实体,他对“实体”概念做了一个界定,实体就是不依赖别的东西、而别的东西却要依赖它而存在的东西。说到底,实体就是具有独立实在性的东西。在笛卡尔看来,精神和物质是彼此独立、互不依赖的,在这种意义上它们都是实体;但是另一方面,它们都要依赖上帝,在这种意义上它们只是相对实体,而创造一切的上帝才是绝对实体。
这样一来,笛卡尔就通过上帝这个宽阔的跳板,实现了从狭隘的自我到广阔的心物二元论世界的过渡。上帝一方面保证了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我们精神世界中的观念的可靠性。上帝把这些观念赋予我们,这样我们就有了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于是,一个依靠上帝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二元论世界就帮助笛卡尔摆脱了怀疑论和唯我论的困境。
对于笛卡尔来说,上帝的意义就在于如下两点:第一,他保证了从狭隘的自我向广阔的心物二元论世界的过渡,还是黑格尔的那句话,上帝只是一个理论的大阴沟,它可以解决一切理论难题。第二,他保证了心物两个世界的独立发展,既保证了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也保证了观念世界的可靠性。笛卡尔认为,精神实体的本质属性是思维,物质实体的本质属性是广延。精神无广延,物质无思维,也就是说,精神不占有空间位置,物质不能进行思维。这两个实体彼此之间不发生联系,物质不能决定精神,精神也不能决定物质,只是依靠上帝的大能来保证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这种观点,就是笛卡尔的古典二元论。
他认为,正是依赖上帝的恩赐,我们具有了一些与生俱来的清楚明白的观念。这些观念的种类和数量并不多,主要是几何学的公理、逻辑学的基本规则以及关于上帝的观念。这些天赋观念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据以进行演绎推理的原则和前提,我们正是以这些天赋观念作为出发点和基本规范,通过逻辑推理不断地获得更多的清楚明白的观念,最终构建起整个知识论的理论大厦。
笛卡尔强调,我们断定一个观念是不是真理性的,就是要看它是不是清楚明白的。这样一来,笛卡尔就以“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作为出发点,以“清楚明白”作为真理标准,遵循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规则,一步一步地推出各种命题或定理,初步创立了唯理论的知识论体系。
笛卡尔的古典二元论认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是不发生联系的,它们各行其道,互不影响,只是依靠上帝来保证它们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但是笛卡尔不得不承认,在人身上,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作用。
笛卡尔本人也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对生理学也颇有研究,因此他不能无视这个事实。于是他在晚年提出,在人身上,物质和精神将会发生交感作用。身体是物质,心灵是精神,二者在人身上发生一种经验性的相互作用。笛卡尔认为,这种交感作用就发生在人头脑中的一个叫作松果腺的器官中。
身心交感说是笛卡尔面对事实不得不承认的一种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却与他的心物二元论处于直接的矛盾之中。心物二元论的基本观点是,物质和精神各有自己的本质属性,各遵循自己的规律,相互之间不发生任何作用。但是身心交感说却承认在物质和精神这两种彼此独立的实体之间会发生某种相互影响,这岂不就是自相矛盾吗?按照心物二元论的观点,物质和精神是各行其道的,谁也不影响谁,所以二者构成了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然而按照身心交感说,物质与精神又发生了相互作用,于是就会引出一个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的、谁决定谁的问题,这就与二元论立场相矛盾了。
笛卡尔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大难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能够保证物质和精神既彼此独立(即不发生相互作用),又相互协调?
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要复兴古代的原子论,试图用原子论思想来解决笛卡尔的难题。说到底,伽桑狄的解决方案,就是要把精神物质化。如果把精神变成某种物质性的东西,那么精神与物质之间的矛盾也就解决了。和古代原子论者一样,伽桑狄认为,所谓精神不过是一种更加精细的物质而已。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二元了,只有一元,那就是物质。
再者,伽桑狄对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的那个“我”进行了质疑。在他看来,那个“我”既然只是一个精神,完全不具有物质性和广延性,那么这样一个精神性的东西怎么可能独立存在?怎么可能具有实在性?对于笛卡尔的上帝存在证明,伽桑狄指出,实际上我们并不是根据一个完满的东西才知道我们自己是不完满的,恰恰相反,我们首先发现自己是不完满的,然后通过把不完满的东西不断地完满化,最后就推出了一个上帝。所以上帝并非“我”的前提,而是“我”的结果。这种观点很符合唯物主义理论——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
伽桑狄的基本立场无疑是唯物主义的,但是他在解决笛卡尔的身心交感说与心物二元论的矛盾时,所使用的方法过于简单。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把精神还原为物质,把二元论归结为唯物主义一元论或原子论。
另一位思想家尼古拉·马勒伯朗士(Nicolas Malebranche,1638—1715)则正好相反,如果说伽桑狄是原子论的近代复活者,那么马勒伯朗士就是柏拉图主义的近代复活者。与伽桑狄把精神物质化的做法相反,马勒伯朗士通过把物质精神化的方式来解决身心交感说与心物二元论之间的矛盾。
马勒伯朗士以上帝作为出发点,认为上帝创造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是相互独立的,在这里,他明显地继承了笛卡尔的二元论思想。但是马勒伯朗士却认为,我们并没有直接对物质世界进行认识,我们只是在与上帝的精神交往中对物质的观念进行了认识。由于上帝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共同创造者和保证者,在上帝的头脑中保留着关于物质世界的观念,因此,我们就只需要与上帝进行交流,无须与物质世界发生联系,就可以认识物质世界。
对于这种身心交感现象,马勒伯朗士解释道,这并非是由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由于上帝的随时调节。
马勒伯朗士的偶因论当然是一种解决方案,偶因论既保证了两个世界的彼此独立,又保证了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而且偶因论不需要借助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经验性的交感,它是用上帝的全能来实现这一点的。但是,偶因论的问题就在于,把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一切事件都推到上帝头上,由上帝来承担,这样一来,上帝就太累了!
斯宾诺莎的泛神论
现在我们转向第二位重要的唯理论思想家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斯宾诺莎可能是我们在西方哲学史上见过的最短命的哲学家,只活了四十多岁。但是这个人的人格非常伟大,成为西方哲学家、科学家心中的道德楷模。
斯宾诺莎的道德境界非常高,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热爱真理和追求自由的精神,那种潜心学问、宁愿受苦也不向权贵低头的崇高气节,使他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堪与苏格拉底相比拟的道德典范。
而斯宾诺莎则直接从神出发。神是万事万物的创造者,是最清楚明白的东西,因此是哲学的真正出发点。但是这个神是什么东西呢?斯宾诺莎明确表示,“神即自然”。当他说神是出发点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认为他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当他说“神即自然”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斯宾诺莎这种“神即自然”的观点通常被称为“泛神论”。所谓泛神论就是认为神内在于大自然中,自然中的一草一木都体现着神性,自然和神乃是同一个东西。
为了说明自然的二元化,他提出了三个基本范畴,即实体、属性和样式。斯宾诺莎关于实体的定义与笛卡尔的定义相类似,也与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相类似,实体说到底就是具有独立实在性的东西,它不依赖别的东西而存在。用斯宾诺莎自己的话来说:“实体,我理解为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到的东西,换言之,形成实体的概念,可以无须借助于他物的概念。”可见实体是第一性的东西,别的东西需要通过实体来得到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斯宾诺莎认为,笛卡尔的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都不是真正的实体,因为它们要通过上帝来说明,而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实体,而上帝或神在斯宾诺莎那里就等同于自然,所以只有自然才是唯一无二的实体。除自然之外,别无实体。神、自然、实体,这三个概念完全是相同的。这个唯一实体就是作为原因的、自由的和创造自然的自然
斯宾诺莎接着又对属性和样式进行了说明。他认为,属性就是实体的本质规定性。世界上虽然只有一个实体,但是这个实体却具有无数多的属性。不过对于我们人来说,只能认识其中的两种属性,这就是思维和广延。由这两种不同的属性,就构成了两个不同的样式系列。凡是具有思维属性的样式是一个系列,凡是具有广延属性的样式则是另一个系列。
而所谓样式,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讲,就是实体的分殊,也就是指那些具体的事物,即作为结果的、受必然性所制约的、被自然所创造的自然。实体是一个抽象概念,样式则是指具体事物,实体与样式的关系是原因与结果、自然与必然、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按照实体的两个不同属性,样式也被区分为两个系列,具有广延属性的样式系列就叫作事物的系列,而具有思维属性的样式系列就叫作观念的系列。
笛卡尔认为有两个实体,即物质和精神,它们各有自己的本质属性,精神的属性是思维,物质的属性是广延。但是斯宾诺莎却认为只有一个实体即自然,这个实体具有思维和广延两种属性(确切地说,能够被我们所认识的只有这两种属性);而样式作为实体的分殊,按照思维和广延这两个属性来进行划分,因此构成了观念的系列和事物的系列。这样一来,斯宾诺莎就用“属性二元论”取代了笛卡尔的“实体二元论”。
这种改变有什么重要意义呢?它的意义就在于,可以比较好地解决笛卡尔遗留下来的那个棘手的心物关系问题。现在已经不再是两个实体之间的对立了,而是同一个实体的两种属性之间的对立。由于观念的系列和事物的系列是同一个实体的两个系列,因此它们之间就具有某种内在的协调一致性。
在笛卡尔那里,两个实体之间的协调一致性是通过经验性的相互影响——松果腺中的身心交感——来实现的,这种经验性的相互影响与两个实体的彼此独立之间就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矛盾。但是在斯宾诺莎那里,同一个实体按照两种属性而区分的两个样式系列之间的协调一致性,不是通过经验性的相互影响、而是通过先验的内在和谐而实现的。这种先验的内在和谐被表述为“一体两面”,就是说同一个自然实体可以分为观念与事物两个系列,从这边看是观念的系列,从那边看是事物的系列。
斯宾诺莎的这种观点被叫作“身心平行论”,它既保证了观念的系列和事物的系列的相互独立性,同时也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协调一致,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笛卡尔的难题。
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解决心物关系的三种不同观点,就可以看出很大的差别。笛卡尔的二元论既要坚持物质与精神这两个实体的相互独立,又不得不承认两者之间的协调一致。他无法解释二者为什么会保持协调一致,所以只能借助于经验性的交感作用,但是这种经验性的相互影响必然与强调物质和精神彼此独立的心物二元论相矛盾。马勒伯朗士试图通过偶因论、通过上帝随时随地的干预来保证这两个系列彼此独立同时又协调一致,但这样的做法显得比较愚笨,这个上帝会很累,而且上帝的协调也是在经验中进行的。
而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实际上是把二者的协调一致性从经验的层面提升到了先验的层面,由于观念的系列和事物的系列是同一个实体的两个方面,所以它们必然具有一种内在的协调一致性。
在认识论上,斯宾诺莎与笛卡尔是一脉相承的。
在笛卡尔看来,第三类观念是虚假的,因为它们是我们任意捏造的。第二类观念是靠不住的,因为它们经常欺骗我们。
只有第一类观念,即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那才是真理性的观念,是真知识的源泉。这种认为只有天赋的观念才可靠、而来自感觉经验的观念是靠不住的观点,就是认识论上的唯理论。
与笛卡尔一样,斯宾诺莎也把观念分为三类。第一类观念是直觉的,也就是与生俱来的,无须进行逻辑推理和感觉经验就可以知道的,他把这一类观念叫作“真观念”;第二类是从真观念出发,经过逻辑推理而得出的观念,即推理的或证明的观念;第三类则是通过感觉经验得到的观念。
他写了一本书,叫“伦理学”,全名为“用几何学方法作论证的伦理学”。这本书完全按照欧几里得几何学的推演体例来展开——首先对概念进行定义,接着设立公理,然后根据定义和公理进行推理或证明,得出定理、绎理等。
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斯宾诺莎也与笛卡尔一样强调“清楚明白”,不过他又加上了一个“恰当”,即真理的标准是“清楚明白和恰当”。所谓“恰当”,就是指怎样从真观念里恰当地推出一些新的真观念,怎样按照恰当的推理原则来建立知识体系。斯宾诺莎甚至认为,真观念本身就是判断真理的标准,正如光明既能显示自身又能显示黑暗一样,真观念本身必定具有清楚明白、恰当的特点。不过斯宾诺莎又强调,清楚明白、恰当只是真理的内在标准,真理还有一个外在标准,那就是真观念必须符合它的对象,这个对象当然是指客观事物。
斯宾诺莎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他的本体论之上的,他的本体论认为观念的系列与事物的系列之间具有一种先验的同一性,二者彼此独立但是又相互协调一致,因为它们是“一体两面”。因此,如果一个观念是真观念的话,它在事物系列中也必然有一个与之对应的真对象,它们之间的相互符合不是由于经验性的相互影响,而是由于一种先验的协调一致性。正是由于它们是同一个实体的两个不同样式系列,所以它们必定是相符合的。
此外,斯宾诺莎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个观点一直到今天还影响着我们的哲学。按照这个观点,一个人的知识水平越高,他对自然界的必然规律认识得越清楚,那么他在自然界面前就越自由。
真正的自由在于对客观必然性的驾驭,具体地说,即事物系列严格地遵循自然必然性,观念系列严格地遵循逻辑必然性,在这两种必然性之间有一种先验的协调一致性。因此,你对必然性认识得越清楚,你的思想和行为就越自由。这种观点后来经过黑格尔的进一步阐发而影响了唯物主义,所以今天我们仍然强调,自由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
莱布尼茨的单子论
第三位唯理论思想家是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莱布尼茨是一个德国思想家,我们发现,一进入德国哲学就非常深刻,也比较晦涩,莱布尼茨就是一个开端。
除了发现微积分之外,莱布尼茨在科学方面还有许多其他建树,他创立了数理逻辑,提出了形式逻辑三大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之外的第四大规律,即充足理由律。
在古往今来的哲学中存在着两个著名的迷宫,一个是关于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的关系问题,另一个是关于自由与必然性的关系问题,后者也可以表述为上帝的正义与世间的罪恶之间的关系问题。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就是为了解决第一个迷宫式的问题,他的神正论(“最好世界”理论)则是为了解决第二个迷宫式的问题。
正是出于对建构体系的执着,莱布尼茨首先从本体论的角度来寻找最基本的单元。单元的问题是困扰古往今来哲学家们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莱布尼茨早年受古代原子论的影响比较深,试图把物质性的原子当作世界的最小单位。但是随着思想的成熟,他就发现原子论是有问题的。这问题在于,作为世界最后单元的东西必须是一个不可分的点,它不能再分了。
但是莱布尼茨却认为,古希腊原子论所说的原子并不是不可分的点,因为原子作为物质实体是有广延的,广延是物质实体的基本属性,而凡是有广延的东西就不可能是不可分的点。
如果真的有某种不可分的点,那么它就一定不能是具有广延的物质,而只能是精神性的东西。于是莱布尼茨就提出了一种精神的原子,他称作“形式的原子”。“形式”一词是借用古希腊的概念,实际上是指本质,“形式的原子”即只具有形式而不具有质料的原子,他又把它叫作“单子”。单子具有原子的实体性,但是却没有广延性,因为它没有质料。简言之,单子不是物质性的实体,而是精神性的实体,它才是一个真正的不可分的点。
莱布尼茨进一步对各种点进行了分析:第一种是物理学的点,物理学的点(例如原子)是实在的,但是它却具有广延性,因此不是不可分的点。第二种是数学的点,数学的点由于不占有空间,因此是不可分的,但是它却缺乏实在性。
于是莱布尼茨提出了第三种点,即形而上学的点。形而上学的点具有上述两种点的优点,它既是不可分的点,因为它不具有广延性;又具有实在性,因为它是一个精神实体。而这个形而上学的点就是单子。
莱布尼茨认为,单子不仅是一个不可分的点,而且具有能动性,即它可以自己运动。
莱布尼茨的单子既然是“形式的原子”,它除了不具有广延性(从而不是物质性的东西)以外,仍然保留了原子的其他特点,如实在性、自动性和复多性(即数量无限)等。单子作为一种精神实体,它的能动性就来自它内部的一种感觉和欲望能力,正是这种精神性的力量推动着单子的自身运动。因此,单子不仅是一个不可分的点,而且是一个能动的实体。说到底,单子是一个能动的精神实体,整个世界就是被无限多的这种单子构成的。
第一,单子没有部分,它不能通过自然的方式产生或消灭。由于单子没有量的规定性,即没有广延,所以单子没有部分。而单子既然没有部分,它就既不能组合,也不能分割。因此单子不能以自然的方式组合而成,也不能用自然的方式使它分解消散。那么单子是怎么产生的呢?莱布尼茨说单子是通过上帝的一霎间的闪耀而突然产生的,这就像今天宇宙学所猜测的大爆炸理论一样,只不过多了一个上帝。当然,只要上帝愿意,他也可以在一霎间把单子全部毁灭。上帝是什么?上帝就是创造一切单子的单子,莱布尼茨把上帝叫作“太上单子”,所有单子都是上帝在一瞬间创造的结果。
第二,单子没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也就是说,每个单子都是自我封闭的,单子与单子之间不发生任何交往,每个单子都靠内在的力来推动自身的运动。这样就使得每个单子都是彼此独立的,单子之间不存在经验性的相互作用。
第三,单子是精神性的实体,它们没有轻重和大小之别,彼此之间不存在量的差别,只有质的差别,这种质的差别就表现为每个单子所具有的知觉能力不同。世界上有无数个单子,单子就像原子一样,数量无限。从最低级的单子到最高级的单子,它们之间的唯一差别就在于彼此的知觉能力不一样。最最低级的单子的知觉能力表现为一种很微弱的知觉,即“微知觉”。
莱布尼茨所说的“表象”,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反映”,反映是指一种客观的映照,表象则是指一种主观的现象。表象不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因为单子没有窗户,它不能反映客观世界,而是自己表象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深深地打上了主体自身的烙印。所以在具有不同知觉能力的单子那里,表象出来的世界是不一样的。比微知觉更高一点的就是知觉,构成动物的单子就具有知觉能力,它们通过知觉来表象世界。然后到了构成人类灵魂的单子那里,知觉能力就上升为反思能力,即统觉了。统觉就是一种更高的知觉能力,它使人可以思考感性现象背后的东西,即思考本质。当然还有比人类灵魂更高的单子,即天使和上帝,他们的知觉能力就更高了,所表象出来的世界就更清晰,直接表象出了世界的本质。因此,具有不同知觉能力的单子反映出来的世界不一样,这不是由于客观世界不同,而是由于主观世界不同。
莱布尼茨提出了一种很高明的思想,他把客体的差异还原为了主体的差异。正是由于主体不一样,所以表象出来的世界也是不一样的。
按照莱布尼茨的说法,物质世界只是单子堆积的一种表象,这里并不是说无广延的单子堆积成为有广延的事物,这不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堆积,而是说有广延的事物只是单子堆积的一种现象、一种主观的表象。
同样的道理,单子堆积在一起呈现出好像是有广延的事物,但是这实际上只是构成我们灵魂的单子的一种表象。由于构成我们灵魂的单子的表象能力远远不能与上帝这个“太上单子”的表象能力相比,因此在我们的表象中呈现为具有广延性的事物,在上帝的表象中只不过是一大堆无广延的单子而已。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无广延的单子堆积成了有广延的事物,而是无广延的单子的堆积结果在不同主体的表象中呈现为不同的形态。这样一来,莱布尼茨就把本体论问题还原为认识论问题了。也就是说,客观世界在不同单子的表象中呈现为不同的现象,单子的知觉能力越强,所表象的世界就越清晰、越接近世界的真实面貌;在上帝这个最高的“太上单子”的表象中,整个世界无非就是一大堆单子罢了。
第一条规律是差异律。这是自然界的一条基本规律,莱布尼茨把它表述为:“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就是说,任何两个单子之间都有差别。
第二条规律是连续律。这也是自然界的一条基本规律,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不作飞跃”,也就是说,任何两个相近的单子之间都不会有截然的间断,都可以插进无数个中间状态的单子。
于是,莱布尼茨就解决了古往今来哲学的第一个迷宫,即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之间的矛盾问题。
在莱布尼茨看来,以往的哲学,要么执着于不可分的点,但是却无法说明连续性,例如原子论就是这样;要么执着于连续性,却又无法说明不可分的点,例如笛卡尔在物理学里所说的充实空间就是如此。只有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既保证了每个单子都是一个不可分的点,又保证了整个单子系列——从微知觉的最低单子到明察秋毫的“太上单子”上帝——的连续性。就此而言,莱布尼茨的确是高人一筹的。
莱布尼茨也谈到了这三种观点,第一是相互影响的观点(即笛卡尔的身心交感说),第二是偶因论的观点,第三就是他的前定和谐观点。在他看来,第一种观点强调两个系列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这是一种流俗的观点。第二种观点实际上是把上帝当成了希腊悲剧里面的“救急神”,一旦戏演不下去了就把上帝搬出来,这样实际上是把上帝的地位贬低了。
而他自己的前定和谐观点则认为,上帝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精神和物质这两座钟校对好了,然后这两座钟就有条不紊地运行下去,彼此独立却又保持协调一致。
单子论是多元论,而不是二元论,每一个单子都是一个实体。
莱布尼茨于是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前定和谐理论,他认为,尽管每个单子按照自己的内在欲望向着更高的水平发展,每个单子都趋向于更高的知觉能力,单子与单子之间又不发生相互作用,但是上帝却是万能的,他在创造一切单子的时候,已经把一种内在的和谐赋予了单子。
这是一种极其美妙的前定和谐,它充分体现了上帝的大能。
莱布尼茨认为,这种前定和谐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他通过一个最大的奇迹,即上帝的先验安排,把一切经验性的奇迹都取消了。但是这个最大的奇迹本身只能借助于信仰,也就是说,我首先必须相信上帝是万能的,然后才能接受这样一种前定和谐理论。
由此可见,莱布尼茨不仅实现了不可分的点与连续性的统一,而且实现了自由与必然性的统一——前定和谐理论既保证了每个单子自由独立的运动,同时也保证了整个单子世界的井然有序。
莱布尼茨综合了经验论的观点,认为我们的心灵既不是白板,但也不是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有一些与生俱来的清楚明白的天赋观念,我们的心灵就是一块“有纹路的大理石”。这些大理石本身有一些纹路,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先天的纹路,所以才能通过后天的加工而雕塑成各种塑像。这些纹路是先天的,但是却要经过后天的加工才能成形。
莱布尼茨认为,我们通过反省让心中潜在的那些东西逐渐呈现出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理性认识过程。对于那些作为禀赋、倾向而潜藏于我们心中的观念,有一个从不清晰到清晰、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发展过程。随着我们的认识能力从微知觉到知觉、再到统觉的不断提高,这些天赋的观念也逐渐由模糊而变得清晰、由潜能而转化为现实。而这个认识发展过程就是理性自身的不断提升和启蒙的过程。因此,当你把自己的理性能力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时,天赋的观念就会在你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地呈现出来。这个时候,外在的经验刺激就成为多余的了,你的理性已经足以认识一切东西。因此,认识论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理性提升问题,理性能力较低的人,必须依靠经验的帮助;而理性能力较高的人,只须凭着理性本身就可以认识整个世界。
这样一种差异是理性水平的差异,理性水平越低的人,心中的观念就越模糊,对象之间也充满了偶然性;理性水平越高的人,心中的观念就越清晰,对象之间就越是具有必然性的联系。由此可见,我们的认识从模糊到清晰,看起来是由于外在经验的刺激,实际上却是由于自身理性能力的提高,这就是理性的启蒙历程。
莱布尼茨认为有两类真理,一类是“推理的真理”,另一类是“事实的真理”。推理的真理就是从最根本的观念出发,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排中律,特别是矛盾律,合逻辑地推出一系列的结论。
事实的真理则是通过感觉经验对外界的事物进行感知和认识,它所赖以建立的逻辑规律是充足理由律,充足理由律可以表述为:如果A真并且可以从A中推出B,那么B真。这条由莱布尼茨独创的逻辑规律适用于经验科学的综合命题,即通过经验归纳而从事物的偶然性联系中寻找到某种动力和原因。
莱布尼茨并不否认事实的真理也具有真理性,但是他却认为这只是一种或然性的真理,其真理性远远不能与推理的真理相提并论。在莱布尼茨看来,一般人由于受理性能力的限制,必须依靠事实的真理来认识世界。
因此,这两类真理的根本区别说到底仍然在于理性能力的高低,如果我们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理性水平,我们就可以像上帝那样仅仅依凭矛盾律而把一切知识合逻辑地推演出来,完全不需要任何感觉经验的介入。
这样一种观点就导致了认识论上的极端唯理论倾向,即无限地夸大理性的认识能力,否定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
这种观点就是唯理论发展到最后阶段的观点,即独断论。
莱布尼茨的唯理论思想到了他的继承者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那里就发展成了一种独断论,形成了“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独断论表现了一种理性的狂妄,它认为理性仅仅凭着逻辑就可以认识一切对象,包括作为实体的灵魂、作为整体的宇宙以及作为创造者的上帝。
休谟的怀疑论过分贬低了理性在认识中的作用,片面强调感觉经验的重要性,否定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其结果是使得知识系统成为一堆杂乱无章的观念和印象的大杂烩;独断论却无限地夸大理性的作用,乃至于认为理性是万能的,仅凭着自身就可以认识一切,完全否定了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这两个极端表面上看正好相反,实质上却殊途同归,它们都犯了同一个错误,那就是都没有正确地认识理性本身。
康德认为,我们既不应该像怀疑论那样一味地贬低理性,也不应该像独断论那样无限地夸大理性,而应该在进行认识之前,首先批判地考察一下理性认识能力。
![图片[1]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哲学】《西方哲学史讲演录》个人摘录(第九讲 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 - AI科研 编程 读书笔记 - 小竹の笔记本](https://img.smallbamboo.cn/i/2025/09/18/68cba8e7b2b8d.jpg)
豆瓣链接: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662629/
说明:本文每一行均为部分摘录,阅读连贯性可能较差,个人存档用,推荐购买正版书籍阅读。
2. 论文总结类文章中涉及的图表、数据等素材,版权归原出版商及论文作者所有,仅为学术交流目的引用;若相关权利人认为存在侵权,请联系本网站删除,联系方式:i@smallbamboo.cn。
3. 违反上述声明者,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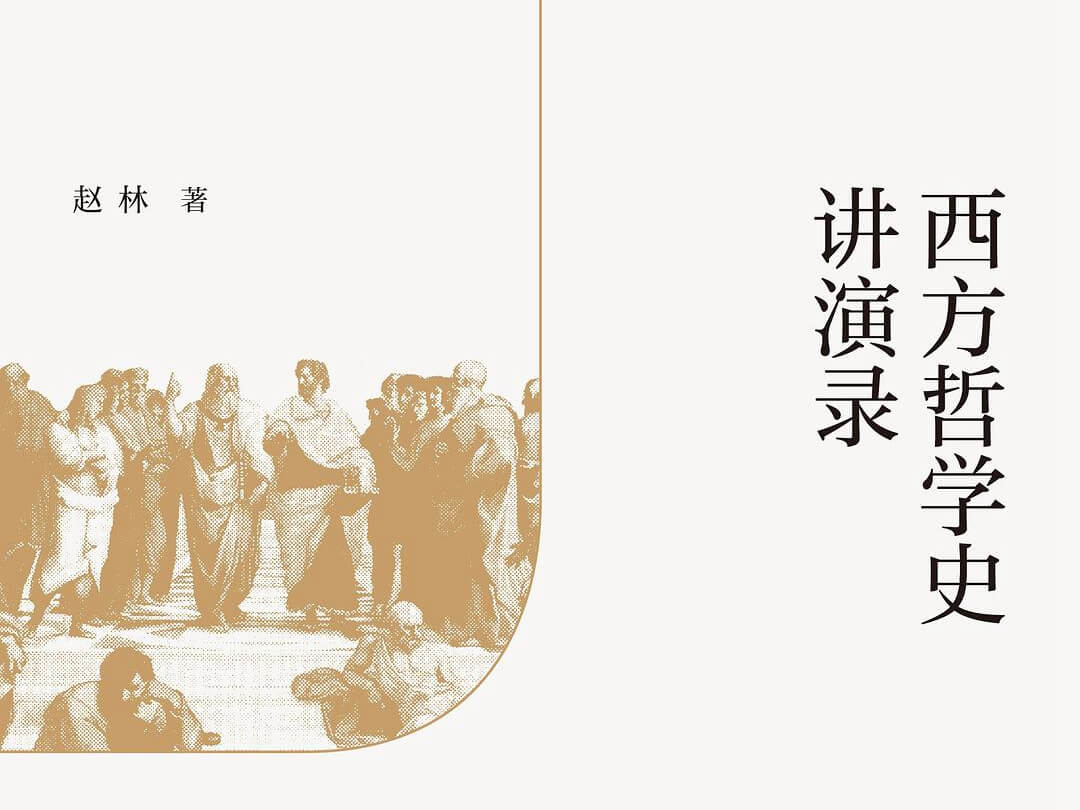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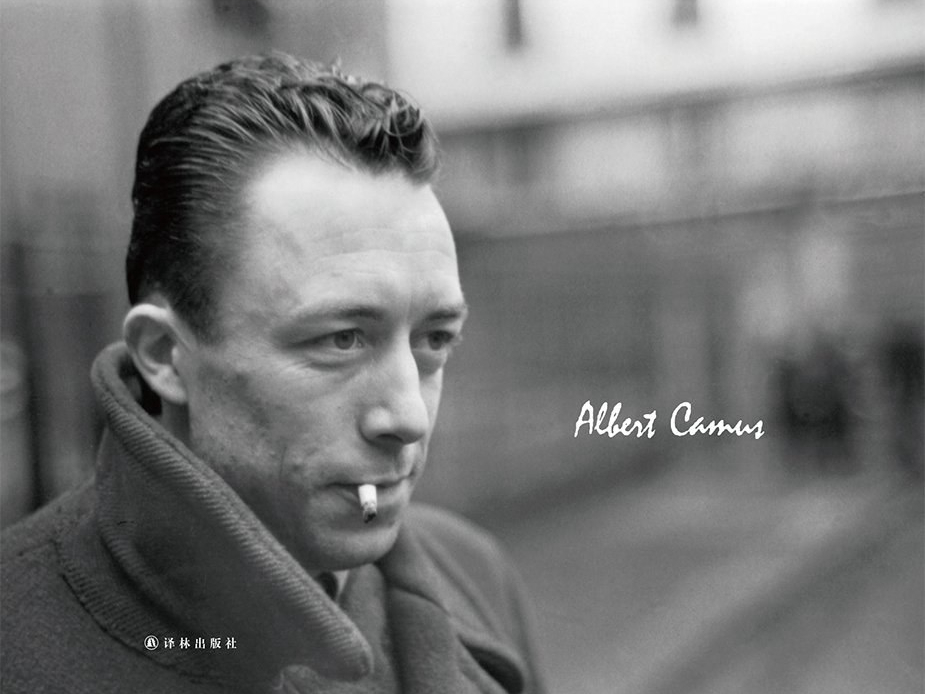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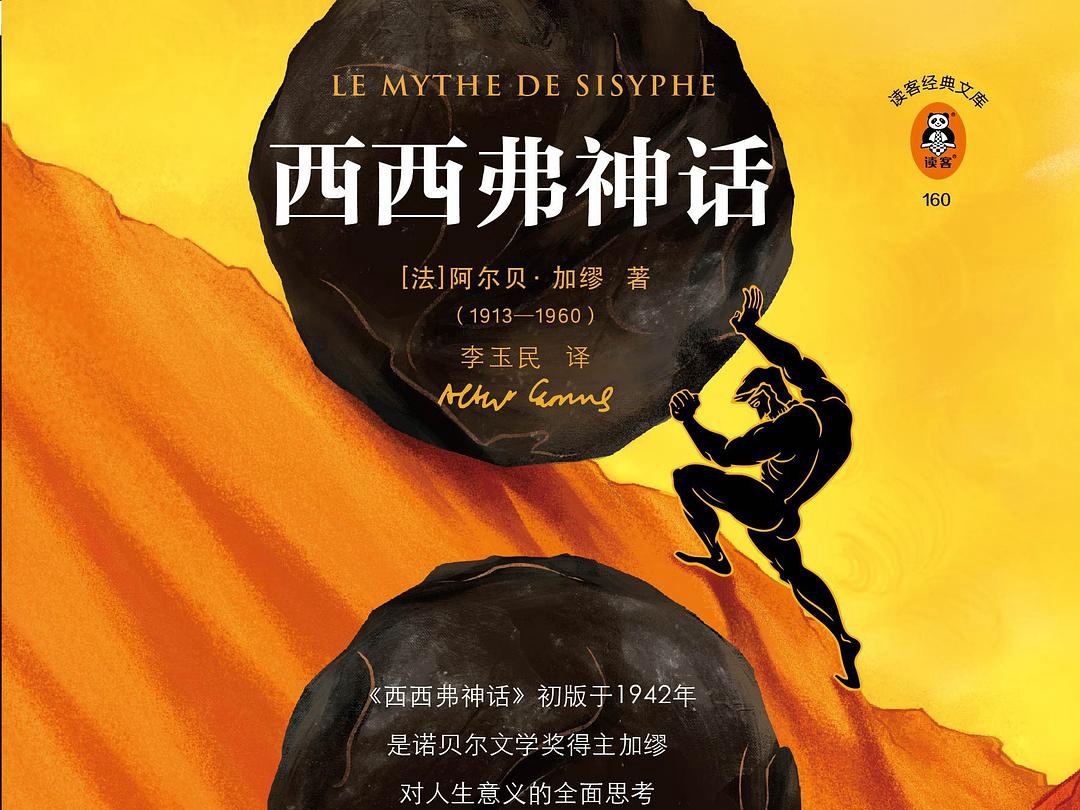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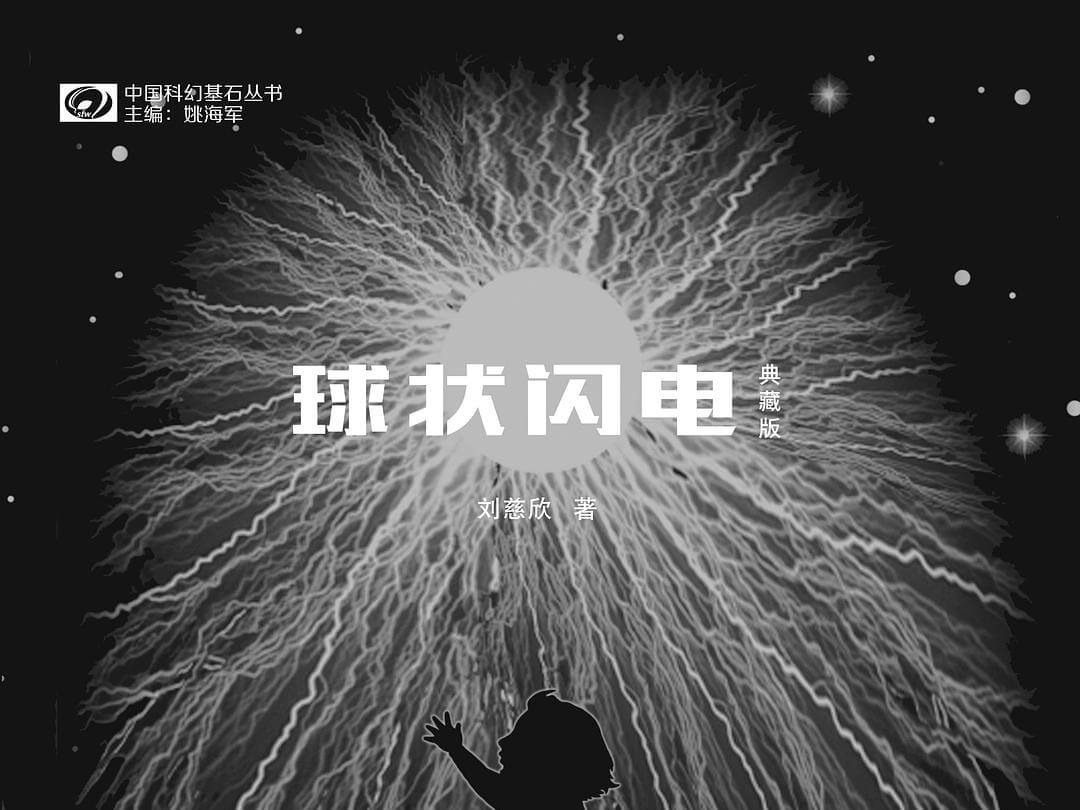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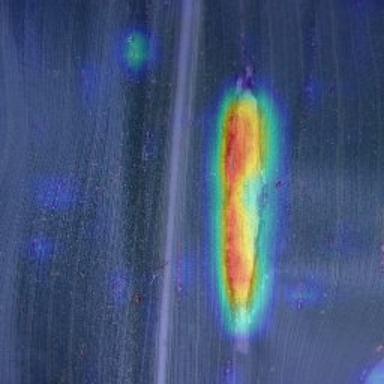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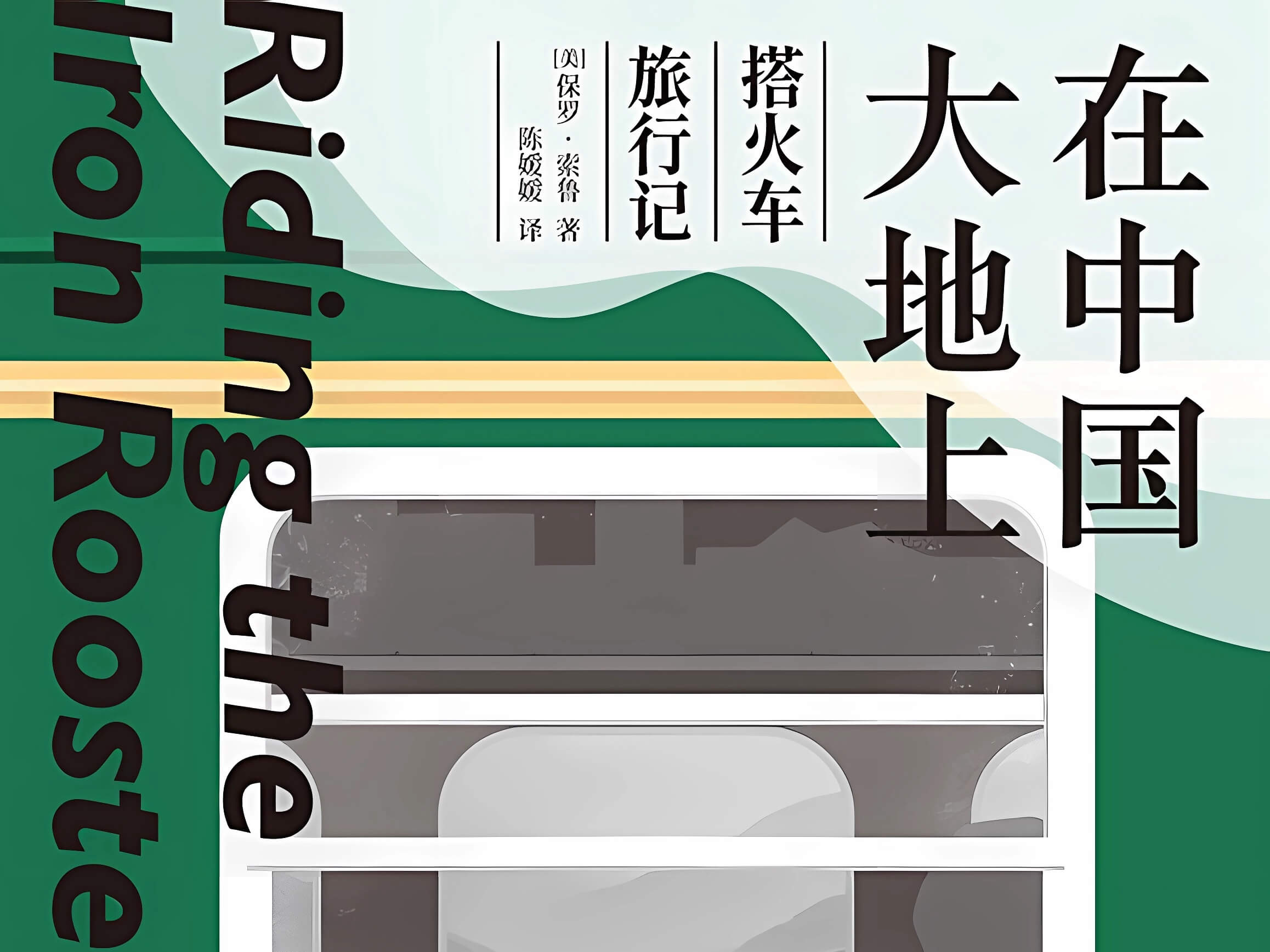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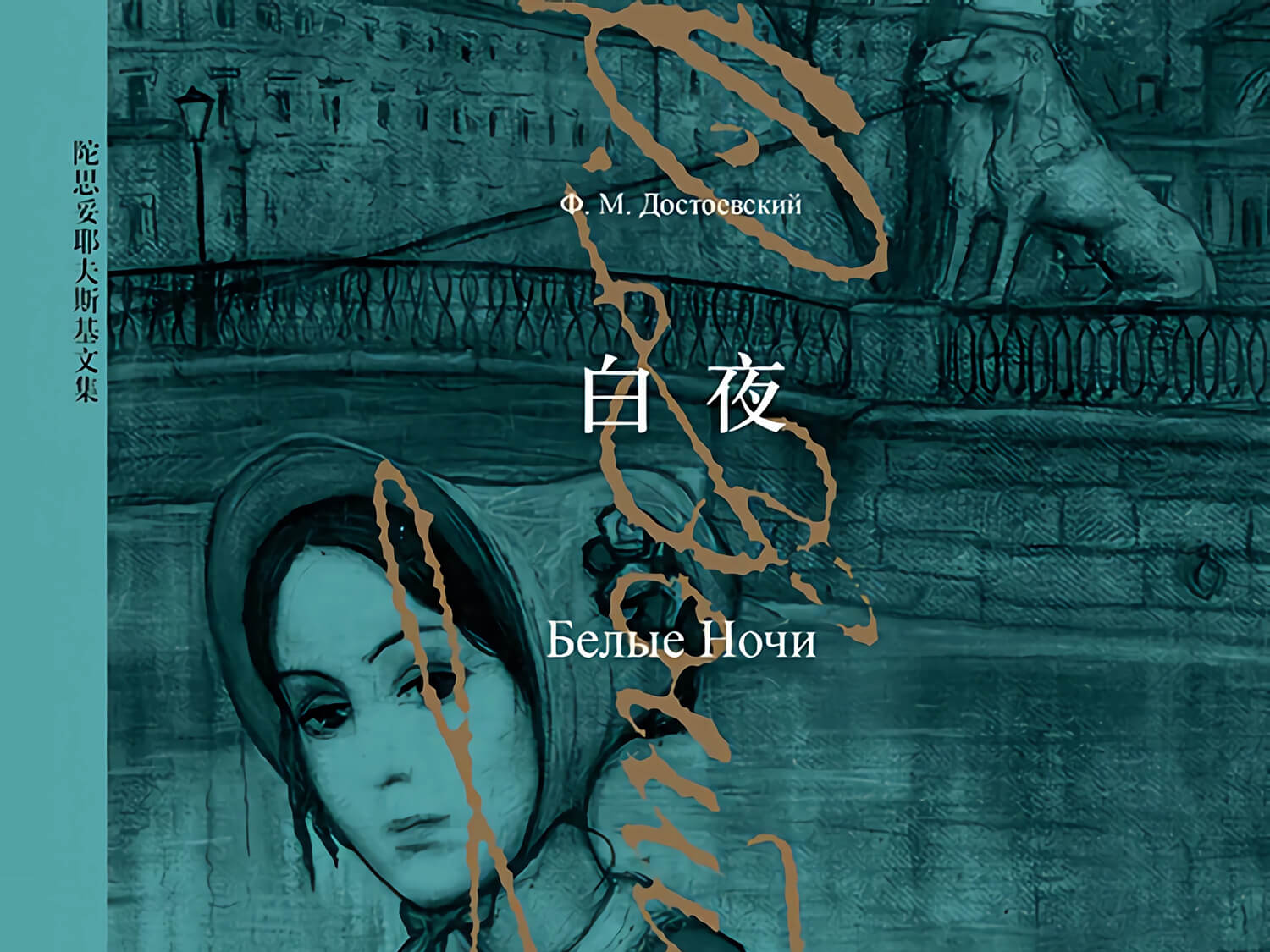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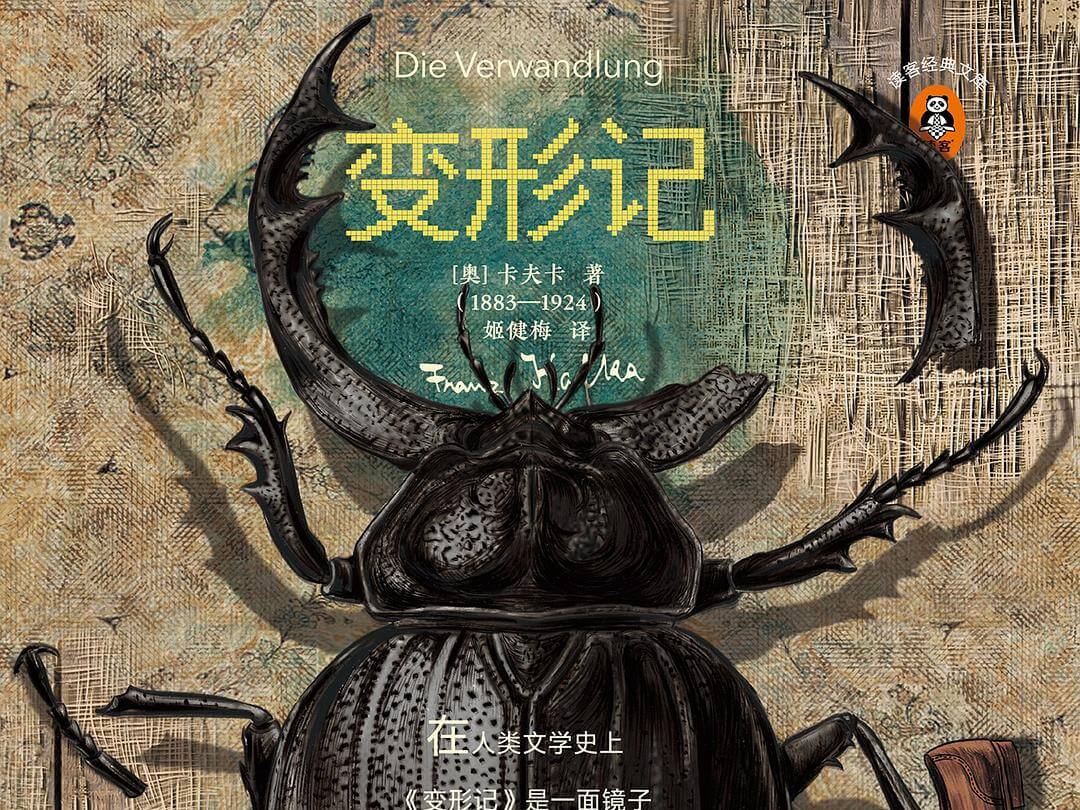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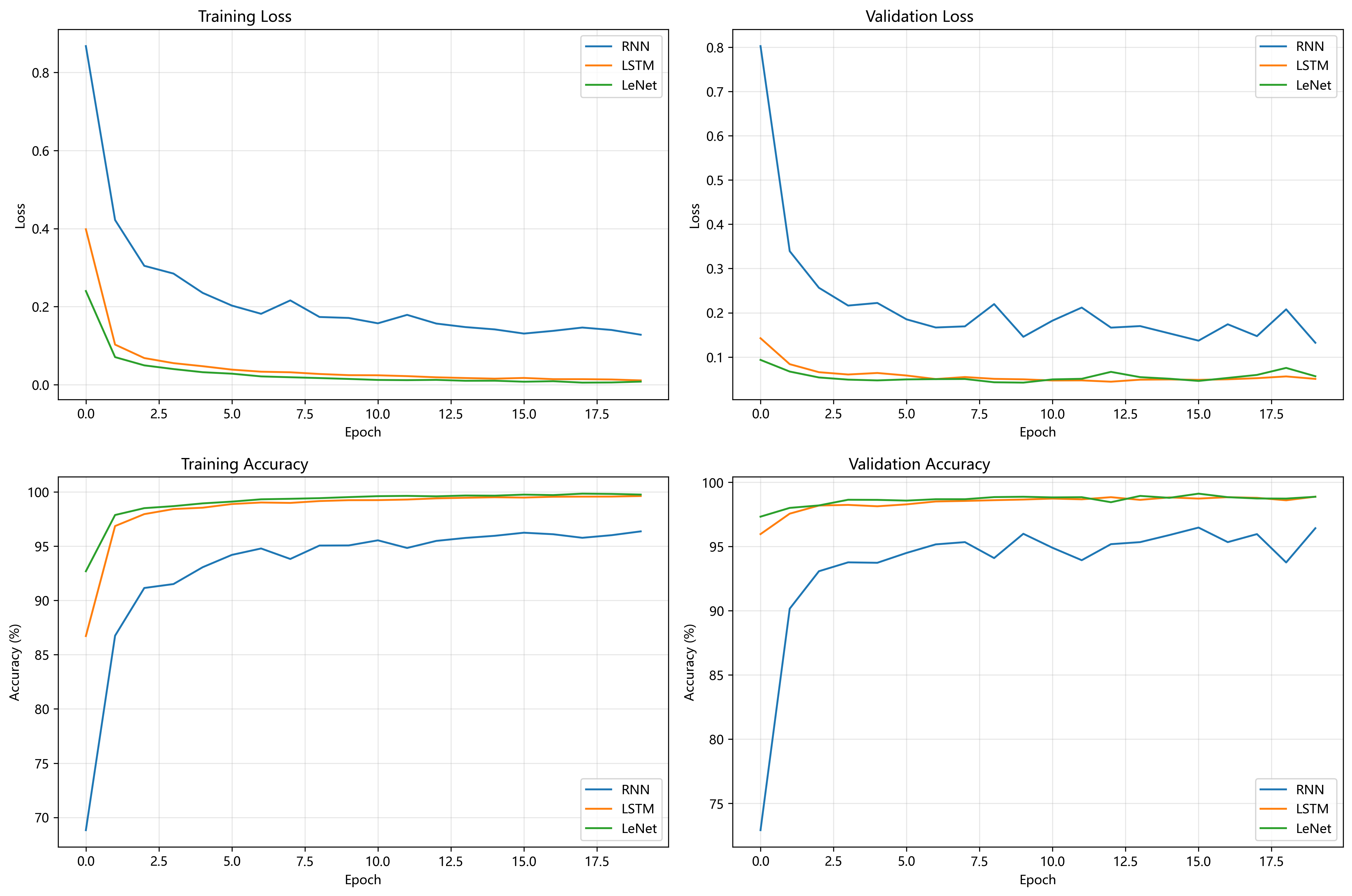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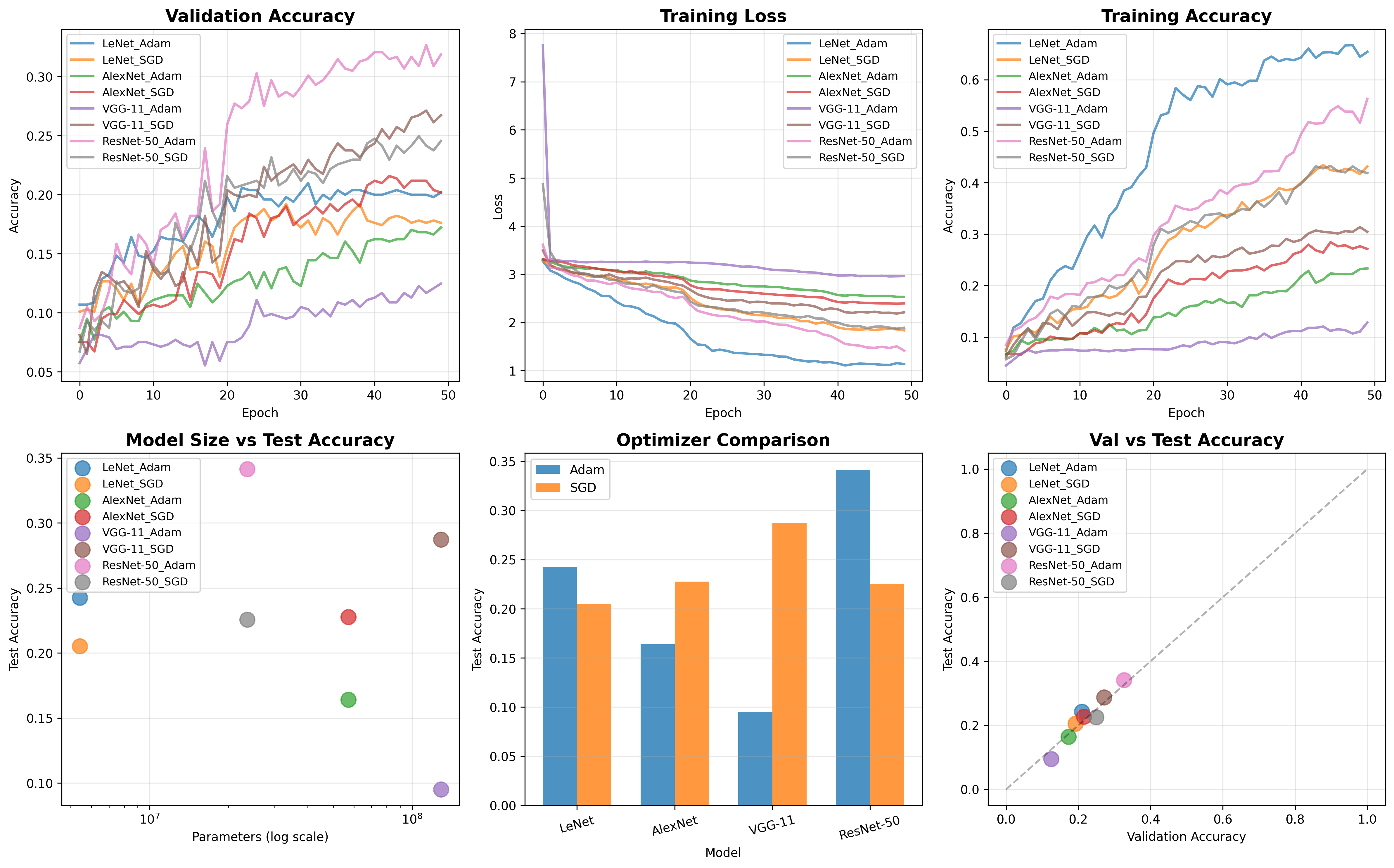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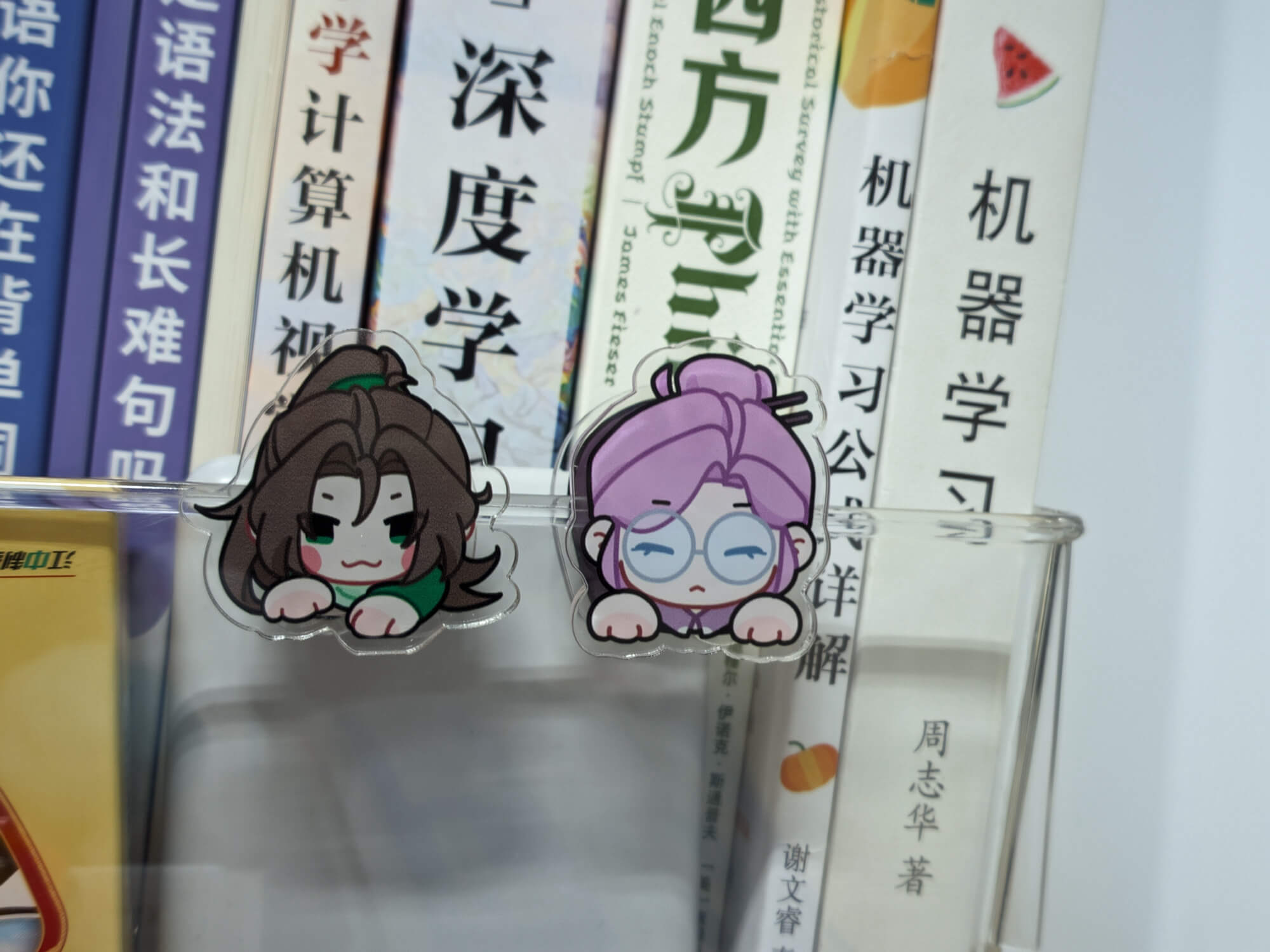







暂无评论内容